斧劈圭立,氣勢險絕,開車的可一法師說:「那就是唐代圭峰禪師駐錫的地方。」沿途經過香積寺、草堂寺、興教寺、靜業寺,分別是善導大師、玄奘大師、道宣律師弘法或駐錫過的地方,令人肅然起敬。在方圓不過幾十裡,竟有如此眾多的在中國佛教史上產生過巨大影嚮的人物,如海會雲集一樣匯集於終南山麓,絕非偶然。
車子嘎然停在林蔭密布的山道上,在這濃密的樹林中,有一條不易為人發覺的崎嶇小路。站在山道上,你只能依稀看到幾間茅棚或聽到人語聲,但你絕然找不到這條路徑,藏得太好了!可一師、張先林和我一行三人背了行囊及今後幾天的蔬菜食物,撥草尋路。跨過潺潺的小溪,再拾級而上就到了我們安居的小屋了。此時太陽剛剛落山,山風吹來,竟如一下子將我們吹到清涼國了,與方才剛出西安站那種灼烈的炎酷判若兩個世界。
終南隨筆:住在雲山深處的隱士
兩年多前,我來此小住過,房後住的那位勤勞的已有七八年禁語的尼師已不知去向。那時她的房門屋後,種了許多的蔬菜供養大眾。我們時常興奮地摘下紅紅的西紅柿、翠綠頂花的黃瓜、彎彎的豆角,她只是遠遠地坐在屋簷下,歡喜地看著我們……
挨著我住的另一位法師聽說還是方丈,屋子收拾的很有些品味,用木板作了個很大的臺子,白天在臺子上喝茶,晚上在臺子上睡覺。他雅好書法,經常看到他揮揮灑灑地抒發著心性。盡管他躲在這裡,找他的人還是不斷。在這個資訊發達的社會裡,像他這樣一個一方教主級的人物想隱居很難。當然也不排除一些想走「終南捷徑」之人。在這莽莽的八百裡秦川中,有七十二個峪口,有各種類型的「隱士」生活著,境遇不同,生活的態度更是千差萬別了。這次來那位方丈也消失了,據說是「走洩」了消息,被他的信眾們「綁架」了。今晚,他睡覺的大臺子就留給我了。終南山許多的住山人都是承接著上一個隱士留下的「家業」。

每天清晨,都是被喧叫在枝頭的各種鳥的叫聲喚醒。傾耳諦聽,它們有的竊竊私語,有的枝椏高鳴,有的相互問著早安,有的高喊著媽媽要吃早餐。在清晨和曦的氛圍中,我時常沉浸在聲樂的海洋裡。同樣是住山的南韓法頂禪師能在一大群鳥的叫聲裡一一分辨出它們分別是甚麼鳥。而在瓦爾登湖生活多年的梭羅先生亦能分辨出湖中的陸地上的各種植物,並巧妙地利用這一切。我的茅棚三面是蔥蔥鬱鬱的青山,我能聽到澗穀中流淌的小溪,能看到第一縷的晨光,穿過前面遮擋大山的縫隙,沖破迷霧,打在對面的山崖上,給這濃濃的墨綠抹上一筆桔黃。我享受這略帶寒意的山風,趺坐山崖,不久打開眼睛,就能感到陽光的挪動,直至太陽爬超高山,將金燦燦的光無私地灑滿山頂。
又是一個雨後的清晨,我和張先生來到山澗穀底。這裡巨石交錯,彩蝶翻飛,山蔭石徑許多是多年人未踏至,芒草沒腰,探石潛行,我們去探尋「千竹庵」的一位好茶的隱士。他寫過一本《嶺上多白雲》的書,自署南山如濟,道出了山中樸實無華的粗茶淡飯中的那種清明自在。不想翻過了竹林幽徑,見「鐵將軍」把門,遙憶兩年前在他的小院中捧著粗瓷大碗吃茶,黝黑的手扒掉皮吃燒土豆的情景似在昨日,草庵前一木牌上書四字「禪悅為食」。
其實我更喜歡紫閣峪的秋天,當通紅通紅的丹柿掛滿枝頭時,楓葉將山巒染得像彩屏一樣。也有石榴裂開了嘴,露出了紅瑪瑙一樣的果實,當它熟透了墜落在地,驚飛了覓食的山雀。我們便由衷地贊嘆天池道人的詩句:山中秋老無人摘,自迸明珠打雀兒。無心為道,大自然的真實寫照無時不刻不在展示著無言的教意。紫雲閣深處築於懸崖上的「敬德燈」在夕陽下更顯出它的尊嚴與氣勢。唐代的杜甫在《秋興八首》寫下了「昆吾禦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美陂」的詩句。
在終南山據說有五千隱士,散居最多的峪口就是大峪。不完全統計有千人之多。其實這裡我先後來過四次,不知是何種緣故,一見到它那勢拔五岳、鬼劈神切的山形就為它折服。獅子岩是虛雲老和尚修行的地方。一日,虛老架起柴火,準備燒一鍋土豆吃,土豆未熟,虛老已入深禪定,這一定竟過去了十幾天。當住在獅子岩虛老的同參來看老人家時,先是發現門口的虎爪印,以為虛老慘遭不測,待進屋看到老人家在打坐,以引磬喚出,虛老脫口問道「土豆燒熟否?」故此這一帶是很多禪和子向往之地。
那一年我是奔著大峪的深秋來的。天光尚曙,老樹嶺秋,穀口寒氣逼人,我闖進了尚未睡醒的大峪。的確,大峪的秋色不同凡嚮,紅得大氣,似天公醉染。此時天氣轉暗,盡管天氣陰晦,我還是鼓足勇氣,披袍前行,卻遙見天空慢慢地有雪花飄落下來,我歡喜欲狂,在風雪裡歌舞足蹈。真是「好雪片片,不落別處」。
此次進山,準備充分,畫具畫夾,筆墨筆洗,一應俱全。昨晚已安營紮寨,晨曦當第一縷陽光照在雄渾的山頭時,我已支起畫板,準備寫生了。早有晨起的山僧在澗邊汲水,覺得頗有「深山藏古寺」的畫意,其實這裡本就沒有大的寺院,隱士們有的就散居在澗水崖邊。正當我揮筆寫生之際,一陣風笛聲從幽穀傳出,有如天籟自鳴。舉頭側望,在散漫這薄霧的山道上,一位身著黃袍的僧人,沿著山道,伴著清溪的歡笑,踏歌而來,吹的是野調,無腔自悠然,道的就是那份自在……
其實,在市場經濟搞活的今天,哪裡有世外桃源,越來越多的農家樂駐進了大峪,不知是哪位領導出國考察引進鱒魚這個品種,於是乎沿溪的大小酒店都在做鱒魚生意。我看到一家氣派的鱒魚館的左右分別是兩間僧人的住房,很是尷尬,哪裡還談得上甚麼「隱居」喲?無奈!很多的隱者們逃向更深的山裡,這種上千年形成的有中國特質的隱士文化受到嚴重的沖擊,那種不知有漢魏、不問甲子、農耕自足、超然物外的生活被快速地改變著。我先後來過大峪四次,這個「春風疑不到天涯」的清靜場所,正快速地蛻變著。幾年前,美國的漢學家比爾·波特寫了一本尋訪中國當代隱士的書《空穀幽蘭》,很是風靡。然而正是這本書的風靡,隱士們的生活就不得安寧了。為了逃避那些進山探訪的各路人馬,隱士們會不停地輾轉搬家。詩人賈島駐足一處人去廬空的茅棚,悵然地寫道:「雖有柴門長不關,片雲孤木伴身閑。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
這樣的結果,可能是比爾所料不及的。這個大胡子的中國名字叫「赤松子」,他經常來黃梅四祖寺,我的恩師慧公上人就接待過他兩次。他現在住在海邊,也過著隱士般的生活。他將中國的寒山拾得的詩翻譯到美國,但沒想到竟引起嬉皮士們的熱捧。寒山大士這種居無定所、岩穴為廬、散曠豁達的生活方式為他們膜拜,甚至奉為祖師,其實也給他們的精神世界註入了新的血液。這一點又是比爾沒想到的。
一連數日,我都奔走在大峪的溝壑之間,我為其崔巍雄奇、大開大合的氣勢震撼著。在宋代,有華原人範寬以望山苦不足的篤誠,來詮釋道家的坐忘、澡雪之操。無論雪雨晴陰,兀坐終南,捕捉那渾闊蒼潤的風骨及細微的變化,完成了曠世之作《溪山行旅圖》(現藏臺北故宮)。在天津藝術博物館,亦藏有範寬另一幅力作《雪夜寒林圖》。我至今還記得十幾歲時看畫的感覺,畫幅巨大,呈頂天立地之勢,佇立其前,幽心細品,便覺冷風撲面,令人齒寒,如臨灞橋風雪。在對景寫生時,我發現沒有現成的技法可用,在這自然的鬼斧神工面前,有些技法是超越意識之外的,是在筆墨轉動的瞬間無意識完成的。我有時癡想,現代人可否能畫出與《溪山行旅圖》比肩的作品呢?應該說很難,沒有古人那種胸臆,也沒有古人那種定力,更缺少那種篤誠的殉道精神。
午後的陽光熾熱異常,但我和張先生還是去了西翠花。順著盤山道一路繞去,幾番盤轉後,竟能看到更加恢闊、比肩排列的峰巒,如蓮花湧出。在一座土坯房後邊菜地裡挖土豆的老漢竟是我兩年前拍到做土豆餅的山民,他憨憨地朝我一笑,那份真誠現實生活中難得見到。穿過好大一片荒蕪的草徑,似撥芒尋古道一般,才現出「終南草堂」的門舍。在社會上有了一定影嚮的《問道》刊物就誕生於此,裡面散落著幾間土坯房,及種種菜蔬花草,確有些大觀園中稻香邨的味道。看門人因我們事先未做安排不速造訪,而把我們擋在門外,說掌門人張劍鋒正在講課。其實又何需問道,道不遠人,植在心源,本自具足,只是我們有時不自信罷了。
當夕陽最後一抹餘暉照在山崖的頂峰,狂噪了一天的蟬開始安寧,蓊鬱的樹木似乎化作濃的汁,裹著草卉之香的山風向我襲來。這時你再傾耳諦聽那小溪的低唱,落花的輕吟……
我也許不太了解此刻地球上其他的人是怎樣生活的,但我確信,可能沒有山中隱士更能享受到這一刻、甚至是每一刻的安寧。山居的隱士大抵是孤獨的,相對又是赤貧的。他們的精神世界正如莊子《達生》篇中所言:「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讀到苗子兮寫終南山隱士生活的文章「住在雲山深處」的一段,甚為精彩:所謂「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正因為隱士們安於貧窮,他們才絕少欲望,才無需對外面繁華世界點頭哈腰、阿諛諂媚。他們昂起高傲的頭立於山林之間,無憂無慮,因為他們相信,飛鳥尚且恣意快活,人又何必將自己困於功名利祿的樊籠?
文:明鑒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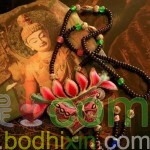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