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裡有一個有趣的比喻,有一群盲人圍著一頭大象,他們試圖用自己的觸覺來感受大象並且向其他人描述自己所認識的大象。不過比較糟糕的是他們有的只是抓住了大象的腿,有的只是抓住了大象的尾巴,還有的只是抓住了大象的鼻子。這樣的結果就是當他們向別人描述大象的時候,偏差的出現就不可避免。在這裡,大象被作為真理的象徵,而盲人們,則象徵那些試圖描述圓滿真理的失敗者。
由於認識上的局限,第一位先生會錯把大象當成是一棵大樹一樣的圓柱體(他只是抓住了腿),第二位先生則認為大象是一條繩子一樣的東西(他抓住了尾巴),第三位先生的看法則是:大象是一種蟒蛇一樣的圓滾滾的東西。假如從一個明眼人的角度來看,這三位先生都講述了真理的一部分,但是非常不全面,這導致他們所描述的真理非常片面,這會導致很多邪見。因為對真理的片面理解是邪見產生的根源。
佛陀就是那位明眼人,而世間其他描述者(佛教以外)就是那些盲人。他們或許講述了一部分的真理,比如把大象說成是一只繩子。但是由於他們沒講出大象的全貌(雖然他們試圖這麼做),這樣的見解並不能導致解脫。因此我們把佛陀稱為真理的發現者並不特別合適,因為其他人也發現了一部分的真理,我們應該稱呼佛陀為圓滿真理的發現證悟者或許更加合適。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在古印度的吠陀經裡也會出現關於輪回的描述(雖然從佛教的角度來說,那並非很精確的描述)。因為在佛陀之前,也有人在試圖尋找真理,他們或許也摸到了象鼻子並且對它進行了描述。而佛陀在描述整個大象的時候不可避免要描述一下象鼻子。但是由於他們並沒有真正的證悟,因此佛教徒並不覺得他們所描述的真理是圓滿的。但是有的人看到這些就斷定佛陀是繼承了婆羅門教的某些觀點並加以發揚,事實上,那只是因為吠陀經的作者和佛陀一樣描述過象鼻子而已。我相信你還可以發現耶穌和佛陀一樣都描述過大象的眼睛,但這不表示耶穌和佛陀的證悟在同一個程度。假如你繼續深入了解悉達多的教法,就會同意他確實描述了很多人沒有描述的東西。但在此之前,缺乏對佛法的深入了解可能讓你認為耶穌(甚至穆罕默德,老子或濕婆神)和佛陀提供的都是同樣的東西。這樣的觀點被視為對教法缺乏了解的象徵之一。
悉達多太子在證悟之後,為我們指出了一條解脫之路,他留下了無數的法門,以適應各種各樣的眾生,假如我們照他說的去做,那麼我們可以獲得與他一樣的成就。(有些密法甚至保證我們在一生之中就可以成就)。佛陀在證悟之後第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們:其實我們和他並無區別,之所以顯現出這麼大的差距只是因為我們被妄想執著捂住了眼睛而已,假如你把那塊妨礙你直視實相的布摘掉的話,你就會解脫並且成佛。
既然佛陀已經為我們留下了一條非常好的解脫之路,那麼我們有何必要去另辟蹊徑。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似乎找到了另一條路,不過這另一條路上往往有老虎在等著你。假如你對佛法有充分的了解,你就會知道,從一個凡夫轉變為圓滿佛陀,這中間的過程並不比你在太平洋海底尋找拿破侖幾百年前扔進太平洋的一只胸針更加簡單,你沒有必要去冒這個危險,而拒絕佛陀的向導。
但是學佛並不表示我們一定要按照固定的形式,佛陀並沒有說所有的人都必須這樣或者那樣。假如一個耳光可以讓你開悟的話(象那洛巴那樣),那麼對你來說,這個耳光就是學佛。不過我們多數人都無法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證悟,因此念珠和佛像的存在就不是不必要的。
有時候我們會猜測佛陀的境界,事實上,以我們有限的經驗去猜測無限本身就是很離譜的事,我們被各種觀念所束縛,當我們聽到一個人可以在茶杯裡跳舞(甚至遠足旅行)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這只是想象力豐富的人的狂想而已。在這樣的束縛之下,不能指望我們了解佛陀的境界。因為你是在以你的極其有限的概念去試圖詮釋(或理解)無限。
假如你要知道蘋果的滋味,最好的辦法就是你親自去吃,不管別人向你如何描述,不管他們使用多麼精確的詞匯,你都無法真正了解蘋果的滋味,你所了解的只是用語言概括的不精確的東西而已。與其對著蘋果猜測它的味道,不如拿到手上咬一口。
事實上,在佛教裡開悟只是被視為初地菩薩而已,他相當於你在黑屋子裡點著了一只蠟燭,借由燭光,你可以看到有限的東西,這樣你就不會撞到牆上導致腦袋疼痛,隨著你修行的深入,你的燭光會越來越亮,所導致的結果就是你看到的東西越來越多,你可以看到各種現象之間的互相依存的關系。你看到的越多,你就越不會被迷惑。成佛就象是燈光大亮。這個時候,你不再有任何迷惑,一切都是那麼清清楚楚,一切都不再需要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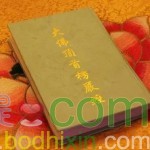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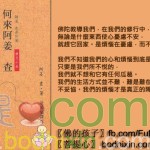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