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把「無常」當成「恆常」。
把所有不能恆常存在的東西,當成是不變的,這是我們眾生的「四顛倒」之一。
內在的身是變化的。
我們身體裡堅硬的部分,屬於「地大」;流動的部分屬於「風大」;循環的部分屬於「水大」;熱量的部分屬於「火大」。這個地水火風四大組合之身,也沒有固定不變
的我。
假如有恆常不變的我,那我們是否可以永遠不長大?
有一部佛經叫《佛說入胎經》,給入胎的人定義一個術語,叫羯羅藍,經中詳細說明了胚胎在一周、兩周、三周等等時間裡如何變化,知道好幾個禮拜,好幾個月,基本的生命形態都完成了,如何分娩。
我們生下來以後,從尿牀到不尿牀,從懵懂無知到善能分別,從善能分別到知識遞增累進,然後到還歸於平淡,來之於泥土,回歸於大地。
有哪一刻,我們此身是不變的?
我們的思想也是變化的。
在人類历史上的哲學思想,有哪一個是固定不變的?所有緣於心的認知的學說,有恆常的嗎?
東方古老的學說,老子的?儒家的?諸子百家的?有可以一成不變的嗎?
西方古老的哲學,從亞裡士多德,到柏拉圖,再到蘇格拉底,直到十七、十八、十九世紀,萊布尼茲、笛卡爾、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採,乃至到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思想……有哪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再看看我們自己的心,有沒有恆常不變的?
每一個念頭,都在特定的環境下。比如在我很喜歡的環境下,吃的無論是面包,還是饅頭,或者土豆茄子,都是如嚼至味;但是受到批評的時候,或者參加討厭的人的宴會,即使吃最愛吃的匹薩、火鍋,都味同嚼蠟。
到底這個如嚼至味的心是你的心,還是味同嚼蠟的心是你的心?
無常生滅的東西依賴各種條件存在,不能獨立做自己的主宰。我們可以來看看這個「無常」是建立在甚麼樣的大前提下的。
比如說,這裡有一串菩提念珠,它由甚麼組合而成?如果我把它的線扯下來,還有念珠嗎?沒有了。我把這些珠子粉碎了,還有念珠嗎?沒有了。
也就是說,這個叫做念珠的東西,是依賴各種各樣的條件而存在的,因緣和合,才成為一個念珠。
那麼某個寺院,某座山,某人的身體,是不是也是這樣依賴條件而存在呢?沒有飲食我們會怎樣?沒有思想我們會怎樣?離開了條件的組合,還剩下甚麼?
所以任何一個事物都如此,遵從無我的原則,依賴條件存在,不能獨立地做自己的
主宰,不能夠由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形狀、大小、顏色、名稱、方位、存留的時間長短……
事物遵循了無常生滅的法則,無我的心念也是一樣,我們因為執著實有而產生痛苦。
也就是說,無論內在的心、思想、認知,還是心的載體,這個肉身,以及這個身心組合的實驗體,跟外在的大自然的瞬息萬變的交流,有一個固定不變的嗎?
所有事物遵從了無常生滅的法則。
而我們偏偏要抓住一些東西不放,這導致的結果,必然是「痛苦」,痛苦是由執著實有而產生。
能重新經历過去嗎?能提前度過未來嗎?
我們對於過去和未來的焦慮、擔憂、恐懼、懸想,百分之百是在做無用功啊。
我們的心念也遵從無我的法則,無我也是在無常的法則下來推進的,因為無常變化本身就是無我的特質,我們如果把無我的心念當成實有,也會又一次痛苦。
過去和未來,和我們的生命當下並不相關。
那麼已經發生的,和將要放生的,與我們有多大程度的關聯呢?
當我們能夠了知,已經發生的和未來要發生的,都跟我生命的當下毫不相關的時候,可以放下這種執取了。
放下了,還需要去打理這些個念頭嗎?
那麼剩下來的是怎樣呢?安住。——當下心安。是「當下心安」,不是「當下安心」哦。
「當下安心」是一個動詞,你還要去「安」嗎?「當下心安」,是它本來就存在的一個結果。
兩個字顛倒過來,在修行上就完全是兩個境界了,一字之差,萬千懸隔啊。
當下心安,不需要去關註妄念。
既然是當下心安,還需要去關註妄念嗎?妄念不存,那麼正念呢?
沒有妄念的過程,自然就是正念,要刻意去營造一個正念,是否又是一個頭上安頭的妄念啊?
在《圓覺經》中,普賢菩薩問釋迦牟尼,如何知身心皆妄?在這部經典裡,十二個圓覺菩薩,請教釋迦牟尼,第一個是文殊菩薩來請教問題,第二個是普賢菩薩,來請教如何以妄還修於妄,以幻還來止於幻。
安住在心的本來面目,本來具足,在聖不增,在凡不減。
我們應該經常在內心提醒自己,我們的心的本來面目,和釋迦牟尼沒有任何兩樣,純淨、光明、智慧、慈悲,原本具足。
這並不因為我墮落為人,或者墮落為畜生而減少一點;也不因為我生為天,或者證了菩薩就會加多一點。它在聖不增,在凡不減。
在生活中,有沒有類似這種「在聖不增,在凡不減」的例子?
構成水分子的東西叫甚麼?H2O。
水變成水蒸氣以後,H2O 到哪裡去了?還在。
水變成冰以後,H2O 到那裡去了?還在。
我們會不會因為水的形狀變化了,溫度變化了,H2O 就不存在了?只是我們這個生命認知能力所看到的有所不同罷了。
如果是這樣,我們還在擔心甚麼?還煩惱甚麼?還擔憂甚麼?還痛苦甚麼呢?
本來無事,當下心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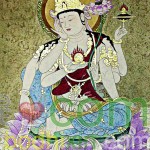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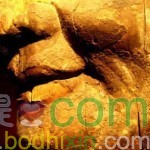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