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有上文學課了,竟然在大殿裡聽了一講。
大學裡古代文學課講詩詞,按年代講,按格律講,按風格講,按詩人講,唯獨少了按境界講。不以境界論,則「禪詩」一類無從涉及,頂多在選修課上提一提王維、皎然、貫休等幾位詩人,或是出於某先生的個人喜好輕描淡寫地講上一講,而中國文學史上那些意境高遠、禪意無邊的禪詩就這樣一次次與學生們擦肩而過。
這未免有些遺憾,不過也不全然是壞事。有時候覺得,描述禪的境界的詩詞,若由缺乏禪修實踐的人來講,更嚴格來說,若由不具備相當境界的人來講,還不如讓它們默然自居,以免有一天成了「第五大俗」。禪師解禪詩,才不至於是個降格的事。
僅將禪詩當成文學作品是不合適的。如同塑繪只是佛像的外在體現,文學也只是禪詩的形態,而智慧才是這些文藝載體的靈魂。
禪詩論的是境界。這裡談境界也並非泛俗地論「XX詩詞體現了XX境界」,如此解析恐怕只是學生應付考試的節奏,朽敗不堪,與禪境真是差之千裡。
禪堂裡論禪詩,如果用《人間詞話》的「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來談,多數人可能要陷入分別的窠臼,以為不是「有我」,便是「無我」,不是「寫實」就是「寫意」。但「有我」、「無我」之境若能如此清晰地區分,恐怕就遠離禪境了。
究竟該將「我」參與進來還是脫離出去?明賢法師指出,中國文豪常常在詩詞文章中,將自己寫得如同旁觀者,記述清晰,而不摻雜個人情緒,不以個人左右環境,而是將自己剝離出來。在禪門中,即便是「有我」,也用得像「無我」一樣。
故「無我之境」雖高,但禪詩中的「無我」並非可以標榜,甚至反而有意在寫「我」。寫「我」,可以將「我」滲透入境,但讀者的感受只是「無我」。以「我」來談「無我」,且游刃有餘,這才是更高的境界。
比如課上講到的無見先睹禪師的一首詩:
一樹青松一抹煙,一輪明月一泓泉;
丹青若寫歸圖畫,添個頭陀坐石邊。
無論怎麼寫「我」,意境究竟是「無我」。
想到過去一個論畫的公案。畫山水畫,要表達深山中有人煙的意境。有三種情況:第一是直接畫出山中之人,第二是勾勒出山林間的茅簷一角,第三是只在山岩曡墨間隱約畫上一縷炊煙。據說第三種畫法意境最高,因為是以無人之景寫人煙之氣,大有「無聲勝有聲」的意味。
這的確是巧妙的構思,但若與「石邊頭陀」相較,顯然這「一縷炊煙」成了王國維所說的「造境」了。
為何禪詩中並不回避「我」?因為對「有我」之人才談「無我」,而人我俱遣、心境不二的境界,何來「我」和「無我」之分?「無我之境」若只是「造境」,那就是大有「我」在,如同「砸碎杯子得到的空性」,睜眼為實,硬說為空。
想起仁淨法師常談的一則現代禪門的公案。臥龍寺的禪堂裡,有禪師甲於放香時大談「無我」。禪師乙見狀走上前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掄去左右耳光。禪師甲頓時從單上跳將起來,大怒:「有本事你用刀子殺了我!」禪師乙聞言笑道:「咦!你剛才還左一個『無我』,右一個『無我』,怎麼這會兒突然冒出個『我』來了?」禪師甲聽後怒氣即止,跳下單來,即向禪師乙頂禮。
故王國維談「有我」、「無我」之境,而在禪師眼中,連這分別也只是「第二峰頭,略容話會」的末後境界,早不是本地風光了。
不刻意區別我與無我,心與外境,這樣的境界其實在中國古典文藝中並非罕見,除了詩詞,早已滲透音樂、繪畫、彫塑中。
在佛像鑒賞課中,幾次談到東方的寫意與西方的寫實,打破了人們慣有的看法——寫意就是表意、寫心,寫實則是寫景、寫境,前者主觀,後者客觀。相反,中國文化中的「寫意」實際上是「註重主觀」,但「客不離主」。
對心的表達並非純粹主觀的事,實際上是主觀離不開客觀。沒有很好的客觀精神,主觀不可能表達得精彩。因為「物我同源」,心與物,主與客不是兩個東西。一人一世界,世界並不在心外,怎可能與心分離?因此,只是外求,也許忽略了對心的了解;只觀心意,則不能準確了解外境。但如果能抽離情緒,那麼對心和世界的了解都會清晰起來。
抽離情緒,做心的旁觀者,是無心而作。沒有貪嗔癡的煩惱,境是境,心是心,都是本來面目,你的世界將是無限的。如果運用到文藝創作上,境界就會大幅提升。所以禪修營期間常談的一句話是「看顏色必生煩惱,用顏色你是畫家」。繪畫、詩詞如此,生活的修行也是如此,因為用的是同一個心。
抽離情緒,才能真正參與;將「我」剝離,「我」反會得到無窮展現。做心的旁觀者,是修行的方法。若能時時觀照,「運水搬柴,無不是道」就不再離我們遙遠。做用顏色的畫家,是美術的修養,若能時時善用,生命的畫作就會精彩紛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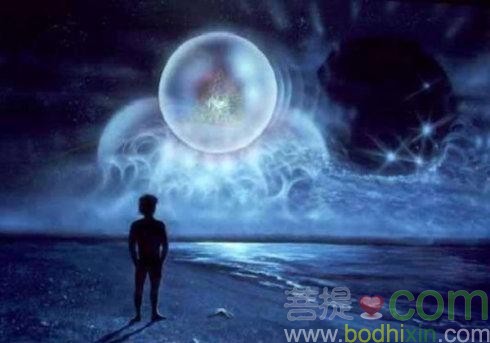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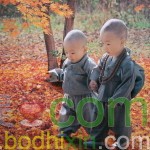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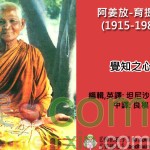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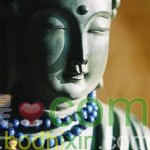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