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本來就是提倡理性與感性之均衡發展的。大乘佛教則更是以「悲智雙運」作為修行的主要原則。我以為現代的佛法修行人,要能在知見上有這一個認識,是頗重要的。否則有可能會走入一些極端。
理性與感性,以緣起觀的角度來看,均是生命的一個部分,本身是沒有甚麼好醜染淨,誰高誰低的。凡夫有凡夫的理智與感情,賢聖亦有賢聖的理智與感情。未修行的人因為覺觀力弱,故理智往往不夠深徹,使感情中夾雜著我見、愛染與煩惱。但理性和感性本身,卻是人生中「隨緣幻現」的東西,不是當被修行人一股腦整個剔除掉的。修行人如沒有正確的見解而想把這兩種東西剔除掉,就易走上「反智識論」或「苦行思想」的偏差。均是不合乎中道,也是很難會有利益的。
反智論的思想存在於佛教發展的後期,也可以說是一種反知識、反思維、反言詮的思想。其緣起是部分佛教徒對禪宗或真常學派的一種誤解,以為知識和思維活動是開悟的障礙。其實真正的禪宗思想哪裡是如此?禪宗講的「不立文字」,是指修行人當能超越文字相及一切言詮的束縛,而能直接在生命中妙悟。並不是說文字或知識本身有甚麼不好。文字、知識如果能束縛人,「不立文字」難道就不能?真能在生命中有四念處覺觀能力的人,見文字就只是文字,不多加甚麼,也不減少甚麼。能在「不增不減」中得自在,才是真正禪宗的「直指本心」,也方才算是妙悟。若一定要把文字言詮除掉而求解脫,這種知見剛好就是一種執取,也剛好就是祖師所說的「死在句下」。事實上文字與言詮本身,本來就和其他萬法一樣,是宛然有而畢竟空,不可得亦不可棄的。它只是一種工具,而工具本身是不具染淨性的。人只要能看出它的緣起性及有限性,而能遠離只知在文字上做活計的心態就可以了。《維摩詰經》中說得很好——「文字性離」、「無有文字」。能覺觀到了這一點,就能走出末代學禪者大氣都不敢出一聲的「反思維開悟格局」,而能自在地用文字表達思想了。否則不但沒有妙悟,反而是「半兩文字重過須彌」。把自己弄得連基本的理性和思辨能力都喪失了。這樣是和佛法最基本的「覺的文化」之精神,背道而馳。久學下去,就會愈學愈獃了!
而反智論的另外一邊——「反感情」之苦行思想,也是一種偏差。佛教若往這方面發展,就容易走上厭世的道路。
有的人本來感情還很正常,一旦修起佛法來,就馬上想把任何感情都一股腦丟掉。好像這些東西有多髒似地。往往還以為自己很精進。其實這純粹是凡夫之見,沒有見到苦與集,反而拿不相幹的東西開刀。以為自己若能做到「不動心」,就是解脫。這實在只是沒有正確知見而造成的幻想而已。
真以佛法覺觀的修行而言,人在該愉快的時候不愉快,該悲傷的時候不悲傷,反而是一種執取,也是人格的不夠成熟。凡夫與聖者愉悅與悲傷的原因不一,方式也不一樣。但只要有真人格的人,一定會有生命中的真感情。該哭而不哭,或沒有感覺,就是中國儒家所說的「麻木不仁」!
我曾因在報上見到一位歐洲的修女,一生獻身中國貧苦百姓的社會與醫療服務工作,而感動不已。後來我把剪報拿給一位朋友看,他馬上就向我數說近代西洋教士「文化侵略」的本質,始自清初乃至近代,如何如何!我當時除了欽佩這一位朋友對历史的嫻熟與對民族文化的珍視外,同時也覺得他少了一些做為一個「人類」的基本東西。我雖然亦自認是固有文化的擁護者,但我卻覺得「作為一個人類的那一些東西」,也就是生命中當有的一些感情,是更為重要的。也就是因為世人沒有這個感情,才會有種族與種族間,宗教與宗教間的沖突、不和。
印順法師曾說過,大乘是比較偏重感性的。我相信這正是對當時太枯索、太偏重思辯的佛教文化之一種反動。我以為佛法的原始面貌,是理性與感性並重的。是要修行人能接受生命,超越生命中的束縛。而所謂超越,卻不是對生命中感性的否定與排斥。佛法修行人當提升及淨化自己的心靈,使自己的感情能愈來愈走出雜染及以一己為中心的象牙塔中,而自然地去關懷周遭的眾生。大乘佛教則可以說是一個特別註重感情之提升的宗教,也主張以實際的利他行為作為平時修學的常課。以此而說大乘在那一個時代,把修行人的生命由純思辯的形上學玄想中拉回世間,而讓人能有一些實際利益眾生的真感情,提倡修行人生命中理性與感性的均衡發展,是很貼切的。大乘也真不愧是當時的佛教現代化與佛法原始精神的複興運動。由大乘的修行理則來看,其註重感性應是很實際的關懷人間及社會,而不僅是一些宗教層面的「宗教情感」。過去中國佛教近數百年的發展,的確是有些偏了,變得太偏重宗教性的出世面,而忽略了大乘入世而服務社會的本懷。近來臺灣佛教界的發展,頗有在這方面能自覺的趨勢,而愈來愈註重社會工作,這是很可喜的現象。我深深地祝願這一個關懷社會與世間的佛教現代化運動,要能看出當初大乘文化流轉中的缺點與弱點,而能把原始佛教覺觀的修行精神帶入教法的日常生活修行層面,才不會再走入過去大乘已走過的老路,也才是真大乘的精神——悲智雙運。
另外就是談到感情,就不能不探討現代佛教中頗有爭議的論題——修行人對情欲的態度。
不可否認的,目前傳統佛教在這一個環節上是比較薄弱的,幾乎清一色地採取一種共同立場——對欲望呵斥、摒除。認為情欲是要不得的東西,必除之而後安。
這個看法嚴正是夠嚴正了,但對一般的在家人而言,卻不夠實際。畢竟人是有頗強的情和欲的,不是簡簡單單地靠呵斥和摒除就解決得了。尤其是在家人之環境和出家人不同,生命中若有了這方面的問題,是無法完全用出家人的態度和方法來處理的。如果一定要,反而會讓一些人有空間去「混水摸魚」,自創歪理。故意去講一些比較偏向放縱的話,去迎合一般人又喜歡放縱情欲,又喜歡開悟證果的想法。其實佛教本身是很可以訂出在家人對欲望的合理修行知見的。既能實際地使在家人的欲望有所軌範,而解除許多不必要的煩惱,亦可使生命中有一個逐漸「離執」的導向。這些都是佛教能做卻沒有做的,或做得不夠好。實屬可惜。
目前的情形不是沒有立場,而是談得太高。教內流行的思想是你如果真的是認真的「修行人」,最好也能像出家人一樣,完全沒有情欲及性生活。結果造成一些在家人的挫折感和不安,也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心理壓力。因為他們做不到。我想後來有一些人倡導「在家佛教」,多少是和此點有關的。
我雖不贊同在家佛教這種二分法,但我極力主張在家人要有在家人獨立的修行人格。切不可幻想自己和出家人一樣。出家人和在家人的修行,雖皆不離佛陀的教法,但在「離欲」的程度上而言,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家人如果不能認清並接受這一個事實,則他的生命中始終會有一種不平衡,也會造成修行的障礙。到最後不是過分自卑,就是過分自高。
自卑的心態是很普通的。造成不少在家人在心理上依賴出家人的習氣,而缺少修行人當有「自依止、法依止」的氣質。要這一種人去推動佛法的現代化,真可說是緣木求魚。這些人一到寺裡見了出家人,馬上就像個乖孫子一般,大氣也不敢出一聲。但一出了廟門,馬上就換了一個人似地,回覆到本來的自我。以我看,這是一種形式的人格分裂。而這種人格最大的的弱點,就是沒有覺觀及承擔的能力,也不可能發揮出佛法的自在精神。
自高的心態剛好就是另一種極端,不但不認為欲望可能有過患,反而特別要去肯定他,好像欲也是一種功德一樣。最近常見的例子,就是有人片面地引用大乘教說中的「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為理由,來支持其「欲望無過患論」。其實這種話誰不會講?自古以來,人類都在想盡辦法替自己的行為找理由。人類學家會創造一種人類學的學說,來支持自己的行為。部分基督徒只要一想到吃肉是上帝準許的,就覺得食肉完全沒有任何不妥,心安理得。佛教徒中有些人一見到大乘經中有這些「金玉良言」,馬上就能舉一反三,自我發揮地去「煩惱即菩提」去了。其實這正說明了人性的悲哀,也充分顯現了人類內心的軟弱和不安。其實一個人想要滿足欲望,何苦一定要去聖言量中找理由呢?這難道不正是一個不安,一個執取嗎?
大乘教義中所說的這些「不二」,其原始的目的是要修行人徹底斷卻了追求世間外之形上解脫的思想。故說生死即涅槃。也是為了要修行人能不畏煩惱,克服煩惱,才會說煩惱即菩提。並沒有說欲望就是解脫。
若要站在原始佛教中四念處覺觀修行的立場來看,佛法並不主張「欲望有過患」,或「欲望無過患」。佛法只是要修行人在自己當下的身心世界中,去體會一個行為真正的原因、作用及影嚮。並不是要人用經中的文字來支持自己的行為。欲望到底是甚麼?是「有漏」還是「無漏」?是解脫還是不解脫?修行人皆當在自己的生命中找答案。這才是佛法中卓然獨立的修行精神。
總而言之,是佛教應界定出在家人對欲望合理的態度。整體的導向應是以「離執」為尊,但不應流於理想高遠而不切實際。要走出不平衡的自卑與自高的心理,先以如實觀的精神接受真實的自己。再在這個基礎上修行,才算是真的精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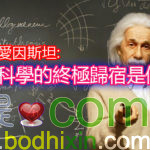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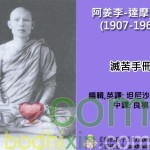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