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類的存在,往往是有著許多苦痛的。這並不是一個宗教傳播者為了傳教而作的灰色悲觀論調,而是一個事實。
講到人生中的苦,當然就會提到佛所說的生、老、病、死。
許多人一聽到佛教講的生、老、病、死,就以為佛教是悲觀消極的,專註意人生中的負面。實際上人生裡這些痛苦的存在,只是一個事實。佛教人以平常心去面對這些人生中的事實,並透過修行去超越因這些事實而造成的痛苦。而人類如果不能超越並克服這些痛苦,就往往會做出一些傷害自己或他人的事。
另外就是人類的好鬥與好戰,為了擴張自我而不顧一切的殘暴面。曾有历史學者說綜觀人類的历史,可以說是沒有一天沒有站爭。尤有甚者是有些頭腦不清的「思想家」鼓吹鬥爭的哲學,以為爭戰是人類「進步」過程中的必然階段。本世紀的兩次世界打戰,皆肇因於一個或兩個民族覺得自己是優秀的強者,而想要徵服其他的民族。於是幾十萬人就侵入他國的領土,殺燒擄掠,無所不為。甚至有一個民族徹底認為另一個民族是邪惡的,而想大規糢有計劃地把該民族完全鏟除掉。
我希望大家不要以為這些事都已「過去」了,以為目前的人類並不存在這些問題。我們人類有一個特點,就是「好了傷疤忘了痛」。事實上這些事距今都不及百年,許多當年受過苦的人至今猶在。我們人類如果不能好好地反省過去並改善自己,很有可能過去的苦痛仍會不斷地再來,只是大家都不知道會在何時何地而已。
撇開历史上的陳跡不談,如果僅就人類目前的現況而言,情況實在也好不到那裡去。現代文明帶給人類的東西,除了隱形眼鏡、試管嬰兒等「方便」外,同時也帶給了現代人更多的近視眼與不孕癥。講求競爭與效率的資本主義社會,除了使人類的「生產力」提高外,同時也使人類時時覺得自己只是市場上一件待價而沽的商品,且隨時皆有被另一件更好的商品取而代之的危險。於是發生了許多的並發癥,焦慮、緊張只是其中的一面,最糟的是人類最基本的精神文明及道德價值意識逐漸破產。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人生就是一場輸贏的游戲,其中沒有對與錯,善與惡。你只要贏了,你就是對的。因為道德或信仰而輸了的人,只是一群傻子,不合適生活在這20世紀的文明裡。
事實上,人的不安及空虛感在急劇地升高。美國人想盡一切方法區阻止販毒,卻沒有辦法阻止人們吸毒。世界各地的自殺率及傷害案皆顯著地在升高。許多人籍著虐待他人來得到「滿足」,其中不少受害者竟是兒童。人們試著用一切方法來宣洩胸中的苦悶,用一切刺激來派遣不安,卻只能暫時緩和以下苦悶的程度,而無法有效地使自己體會到生命中本來有的喜悅安和。就象市場上的頭痛藥一樣,每一種都可使人暫時不頭痛了,卻沒有任何一種可以使人今後永不頭痛。聰明的人類在嘗試使自己比較愉快時,往往變的無力而笨拙,不知如何才是快樂之道。
這就是這本書的目的———–希望人們能通過先哲的智慧及由其中而生的修行方法,使我們加深對我們自己的了解與鍛煉,找出人性中之病根而加以根治。提高人性,解決人類的問題。
提升人性的方法有許多,當今世界上的各大宗教皆以在發揮其影嚮力而做了許多貢獻。我並不覺得佛教是人類「唯一」的希望,但我覺得佛教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就是人類問題的解決必須要透過人類自身的智慧。而本書所要討論的主題,就是人類的先哲之一—佛陀所提出的提升人類智慧的方法。
念處,就是釋迦牟尼佛所教的修行方法—四念處。
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有一個小國的太子,名叫悉達多。因為目睹人類及生物界中種種互相迫害的行為,及生命本身具有的生、老、病、死等苦痛,決定出家學道,希望能找到一種方法來解除眾生的苦惱。經過6年的學習、探索及自我實驗,他終於悟出了宇宙人生的真諦,並因此而知道人類到底當如何認知及自我訓練,方能徹底的由一切牢籠中解放出來,在當時及後來由許多人實驗後,證明為非常有效、真實不虛,故佛教徒尊稱他為「覺者」(覺悟出人生真諦的人),也就是梵語的「佛陀」(BUDDHA ,簡稱佛)。佛弟子把他的言教開示,作整理及集結,就有了「佛經」。在佛經中記載了許多佛所說過的話及佛所經過的事。在佛說過的話語中,包含了許多他所體悟到的道理,其中最主要的基礎就是「緣起法則」。而他所提出的修行方法,最主要的就是八正道。四念處是八正道中的修行方法之一。
所謂「四念處」,其實就是四個修行中觀察覺照的對象,分別是身體、感受、心的一般狀態及心中的思想觀念。佛要修行人在這四個地方(身、受、心、法),均能對現象的起落觀照清楚而不染著,就是四念處的修行。
我們往往有高遠的理想及複雜的思想,卻沒有能力讓一些簡單的事情付諸實現。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會有人類能登陸月球及造原子彈,卻不能免於貧窮及戰爭的威脅的現象。四念處修行方法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要修行人時時直視自己的生命,看清自己真的是在做甚麼。使人類真的「見到」自己在做甚麼,我覺得這是解決人類問題所迫切需要的。以這一點而言,佛所提出的四念處修行方法,是尤其彌足珍貴的。
有理想而不能實現,最主要是因為能力不夠。以佛法的觀點而言,人類有兩項基本潛在的能力,是應該被鍛煉而發揮出來的。一項是認清真相的智慧;另一項就是關懷他人,願為他人服務的愛心—-也就是慈悲。在佛法中,智慧及愛心均是一種「能力」,是可被修行人經過自我的反省及訓練而具備的東西,是人人皆可達到的。人不需要相信一個宇宙中至高無上的存在,也不需要和另一個身外的存在或境界相結合,就可以達到具有智慧及愛心兩種能力的人格。也唯有當人類的智慧及愛心皆成熟到了一個程度後,人類的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故當佛陀用其智慧在深入觀人類的苦難時,他所採取的態度是非常合理而科學的。他認為除了人類自身能努力去反省並鍛煉自己,而提升自己的智慧及慈悲外,並沒有第二條真正實際可行的路。這就是佛在兩千多年前給世人的教誨。
佛法真正的可貴,在於其實際。實際的話不一定那麼美麗動聽,但卻可行。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每當我閱讀佛說過的話,仍會如此深刻地被佛的智慧及慈悲感動,深深地覺得他才是真正的革命家。因為他所面對的,是人類的人格及心靈。
故以我看來,佛法是濟世之學,佛教則是能發揮人類潛在能力的宗教。而八正道及貫穿其全體的四念處修行法門,就是一個非常實際可行,且可提升人性的自我鍛煉法。
鑒於此一法門為佛所開示修行的主要方法之一,但由於佛法流傳久遠,又和許多不同的文化相融合,於今此一主要法門已逐漸為人忽略及淡忘,故近年來我專門從事此一法門之研究與探討。
研究與實驗的結果,發現此一法門不但是原始佛教中修行的主要方法體系,其修行的理論更是佛所開示的「緣起」、「空」、「中道」等教理密不可分。由於對「四念處」的探討,我發現了佛所開示的理(即理論,如緣起、空、如幻等)與事(即修行)的一體性。我發現修行如果忽略了四念處,本來一體的「理」與「事」就容易分開,令修行人走上歧路。偏重理者走上「空」的理論研究但在修行上不知如何應用;結果形成佛法的「玄學化」。而偏重事者容易走上「定」的修行,但不知「定」了以後要如何,在生活中又如何;結果往往形成佛學中的「神祕主義」,以種種定境為解脫。至於「理」上高談「空」及「緣起」,而「事」上只重修定卻不修四念處,就成為理論是一套而實際又是另一套,兩個連不上。勉強連上了卻不得力,總覺得有些障礙。
說四念處是佛教中主要修行方法之一,不但不過分,反而仍嫌不足。凡讀過《念處經》的人都知道。四念處不只是一個方法,而且是一個包含極廣的體系。就連不淨觀及修定的數息觀等,皆包含在四念處的體系中。他詳細的說明了佛法修行人在日常生活中修行的方法、態度、層次等一切細節。我可以肯定的說,佛在世時,佛及佛的諸大弟子(如大迦葉、舍利佛、目楗連等),在日常生活中主要的修行內容就是四念處。在當時「修行」和「四念處」幾乎可以說是同義詞。
象這樣一個重要的修行體系如果被佛法修行人所忽略,無疑地佛法的原始精神就逐漸凋敝了。佛法流傳了兩千多年,方便善巧地引進了許多其他文化中的東西,使更多人能有機會接觸真正的佛法,這固然是佛教慈悲的表現;但在慈悲與方便之間,更重要的是不是忠實地保留存佛法原始的精神與內容呢?如果佛教根本已不再保留有原始的精神與內容,所謂的「慈悲」與「方便」是否仍能成立呢?
我無意批判任何佛教中的宗派或法門,因為一切的法都是「緣起」的,任何宗派的形成一定有其历史上的原因與其「時代意義」。文化皆因能兼容並蓄而成其大,佛法當然也不例外。但我以為兼容並蓄的同時,必須要能保留這一文化的精髓方能名其為「方便」,否則就不是方便而是「變質」了。佛法的「玄學化」與「神祕主義」色彩的介入,逐漸地使一個本來非常平實且能在日常生活中被應用的東西變了質,結果使世界上大多數人都對佛法有了不正確的印象。「玄學化」的結果是使許多人覺得佛理是一種高不可測,又不著邊際的東西。「空」、「不二」的理論雖然也有道理,但總令大多數的人覺得無法用於生活,且和生活沒有直接關系。而「神祕主義」的加入,則形成了佛法世俗化的另一面,其影嚮是使知識分子覺得是一種迷信或多神崇拜;而置身於神祕主義中的修行人,因缺乏佛法中的基本正見(正確的見解),大都不知如何用功。結果修行雖然努力,但皆徒勞無功。
「玄學化」與「神祕主義」,是今日佛法中的「二邊」(即兩個極端)。生於今世的佛法修行人,想要完全不落此二邊,真是難之又難。因為人是環境的動物,而「玄學化」與「神祕主義」,已在佛滅度兩千年後的今天成形且成熟了。人在傳統之中,必然會受到傳統的影嚮。
難雖然難,卻不代表完全不可能。佛法中沒有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一百年累積的枯柴,一把火就能燒掉了。兩千年形成的謬見,明眼人一語就能道破。難只難在修行人有沒有一個「直心」,能不能虛心,耐心地學習及自我實驗。
一般來說傳統的中國佛教徒所了解的四念處,均是以「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為主的。而事實上這種觀法是四念處經過流變以後,被重新包裝與定位後的產物,根本不能代表原來的四念處。這種流變使得本來一個非常活潑且在理論上十分深刻的修行方法,變的獃板而有教條主義色彩,自然也就使此法門變的膚淺而極具遁世傾向。故重新扭轉這一個看法,使讀者能直接了解佛教中的四念處,是本書的目的之一。本書將以南傳佛教巴利藏的《念處經》為主要依據,作為介紹及討論的基礎。
雖然以南傳的經典作為主要依據,但本書所欲介紹的四念處修行方法,仍會有一些地方和今日南傳佛教所教授的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因為我本身是中國佛教徒,故大乘佛教的精神自然會影嚮到我對原始佛教的認識。但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當我越深入四念處的修行,就越覺得今天大家透過《阿含經》及巴利藏所了解到的原始佛教,實在是頗有濃厚的厭離及出世的色彩的,而四念處本身卻並非必然如此。我覺得大家如因為历史上文化環境造成的原因而忽略了四念處,實在非常可惜。而且因為「方便」而忽略了「究竟」,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不正常的現象,是值得為有志於研究佛教現代化的修行者深刻思索的。故我寫此書的另一個目的,是提出一個以當今人類的現況為著眼點,而適合現代人修行的四念處。它的理論和精神仍是依據《念處經》,但在整體的修行心態上而言,的確是很和今天的南傳佛教有一些不同的。
總而言之,我以為對四念處的忽略及討論之不夠精到、完整,是佛法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佛法對全人類來說,卻是有著許多無可替代的珍貴價值的。佛法提出幾個簡單而直接但又非常深刻的智慧理念,直指人類之病,又提出了解決的實際方法。故我以為一個更光明的人類未來,實在是頗需要這一個古老的人類智慧之學的複興。我不敢以佛法的複興者自居,但佛法的複興卻是我及許多佛法修行者深切的期望。我謹希望能以自己的有限的所知,引起大家對四念處的重視及研究的興趣。故寫此一專論,以《做個喜悅的人—念處今論》名之,希望能對佛所開示之「念處」修行方法,作一系列現代化的由淺入深之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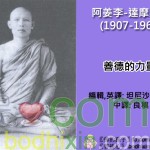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