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離上師
對於修行人來說,暫時與究竟的一切功德之源泉就是上師,大格西博朵瓦是這樣說的:「攝集一切竅訣的基礎就是不舍棄殊勝的善知識。」因此,我們必須做到如影隨形般依止、一剎那間也不離開上師,格西又說:「如果不離上師恆時追隨,那麽此人已經擁有了一切佛法。」依此而言,我們必須恆常不離上師。
可是,我們中的有些人最初在上師前只求得零零星星的傳承,馬上口出狂言說「我要去寂靜的神山了」。其實他根本不能獨立自主地修行,卻一意孤行,這種現象也是極爲普遍的。當上師健在期間,我們這些初學者應當像諺語中所說的「小孩拉著母親的衣襟」一樣瞬間也不離開上師。那麽這樣做到底有甚麼必要呢?第一通過聞思教言可以斷除增益;第二言行舉止莊嚴如法,不放逸。長久依止上師便可對所有好的品德言行都一清二楚、了如指掌,隨學上師極爲重要。
我們在隨學上師的過程中,盡力做到清心寡欲,不爲欲望所惱,最終達到像日月執行那樣逍遙自在地周游神山靜處的境界時,不固定住於一境,也不要說這個地方是我的地方而執爲我所,像野獸一樣對任何地方都毫無貪執。
最初依止上師,在師前安住之時,要以他的確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師之心態恭敬依止,自己的一切所作所爲都不能擅自作主,要謹遵師言,一切威儀十分莊重。所有事情均需請問上師,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自作主張,草率而行。如此一來,自己的所作所爲均成了依教奉行,功德利益很大,並以此可將以往所造的一切罪業悉皆淨除,自己的三門一切所爲不致於放蕩無度,也不會重新累積身語意的罪業。因此說,依教奉行的意義格外重大。
我們的一切行爲既不能違越上師的言教,又要與同修道友們始終持久和睦相處。依照加行中所說的在上師面前聽受包括道次第修心等自己所實修的法門在內的一切教授,必須像蜜蜂享受花蜜的甘美味道一樣以聞思斷除增益懷疑。
晉見上師
如果自己有教言上的疑問要請教或者有事匯報,需要去晉見上師前,就必須搞清楚上師此時是否在百忙之中,是否心情愉悅,在上師悠閑自得、舒心悅意時可以前去討教,而在上師事務繁忙、心緒不佳時萬萬不可莽撞去打擾,就像小馬駒或小狗崽對待它們的母親那樣。在未得到上師的開許之前,自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搖大擺地來到上師面前,由於根本不知曉此刻上師是否心情很好,倘若正巧趕上上師心情不好,那麽就會導致對上師不敬以及擾亂上師的心這兩種極其嚴重的過失。
因此,首先應當到上師的侍者前詢問可不可以前去拜見,了解上師心情好不好的狀況,再以晉見上師尊容比獲得如意寶還難的心態來到師前,對上師毫無怠慢之心、謙虛謹慎、畢恭畢敬,如此可得到廣大的功德。所以,到上師的面前時,先讓侍者去請示上師獲準後方可前往,這一點是極爲重要的。
可是,有些人對此卻不以爲然,他們說:我們既然已經依止上師,所以隨意到上師跟前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不可以隨便去見,那麽依止上師有甚麼用呢?這說明他們壓根不懂依止善知識的方式。例如,世間上那些官員所屬的百姓們也沒有說「因爲他是長官所以甚麼時候想去都可以」而隨便前去見,那麽對於法主、法王、如意寶般妙法源泉之上師,懷有不敬之心,口出非禮之詞說「不管上師開不開許都要去見」便徑直而入,這是對上師的最大不敬。再說,就算是要去拜訪世間的大官員、大人物們,也不能亂了方寸,而必須首先通過他的下屬,依次引見,否則也不能見到。對於上師竟然都不能像世間人對待大官員、大人物那樣尊重敬仰,那還有甚麼比這更不恭敬的態度呢?自己只是私下認爲拜見上師是天經地義、理所應當的事,於是趾高氣揚地直入其內,這種草率舉動恰恰將他無有將上師視爲真佛的清淨觀之內相暴露無遺。
真實作想
本來,我們應當有見一次上師的尊容、聽一次上師的言教就如同親睹佛陀的金顏、親聆佛語一般極爲稀罕難得的想法。如果沒有這樣想,那就是一大錯誤。即使心中確實已生起了面見上師的身相與聽受上師的教言極爲不易的念頭,但是在去往上師面前的途中仍然需要如是憶念:我的上師的的確確就是真正的佛陀,我今雖有這樣的問題要請教,卻不知能否如願以償,假設有幸在上師面前討教,並獲得了滿意的答複,那真是太有福報了。面見一次上師的身相,就相當於親眼目睹了所有佛陀的身相。如此可以清淨無始以來多生累劫中所積的一切罪障,實在具有廣大深遠的意義。之後,在侍者尚未通知上師是否準許之前一直耐心等待。
按理來說本該如此,然而我們這些人即便是一百次見到上師的身相、一百次聽聞上師的言教,仍舊將上師看成是一般的普通人,從未體會到親見上師的身體難得、聆聽上師的 教授難得、見師身聞師言意義重大這一點。如此一來,勢必會導致自相續原有的一切聞思修行功德無餘喪失、前所未有的功德不會重新生起的不良後果。博朵瓦格西曾說過:「對上師不恭是失去智慧的主因。」
如果偶爾因沒有得到開許而未能如願面見上師,也不能心煩意亂,心里應當這樣想:我應該明白這是對自己最殊勝的教誨,這明明是在暗示我:因爲你的惡業罪障太深重了,你若誠心誠意想見真佛上師,就要淨除自己的罪障。
如果一請求即刻得到開許,自己應該想到:在自己罪孽業障尚未清淨時,上師就慈悲恩準前去面見,這說明他老人家一方面是在用強制的方法淨除自己的深重罪障,一方面是爲了讓自己積累廣大的福德,現在有幸去參見上師,應當趁此機會積累福德,於是心里一邊默默觀修七支供,虔誠祈禱,一邊恭恭敬敬地向上師獻上曼茶羅等供品。
倘若上師聲色俱厲地對你進行訓斥呵責,那麽要認識到這是上師在賜給自己竅訣;假設上師大發雷霆,對你大打出手,你也應當認識到:他老人家是在顯示採用強制性方便法淨除我的罪障、摧毀我的煩惱這一事業。長期如此串習,平時也必須與上師形影不離,集中精力精勤修學依止上師的方法。
斷顛倒想
對此有些人顯出一副頗有見地的神態說:就像如果與火靠得太近必將遭到焚燒一樣,如若與上師過於親密,那必然會出現矛盾重重的不良後果。所以,求法時依止上師,在不求法時就遠遠避開上師,到別處去安住,這樣還是很好的。說完便在距離上師一個月路程的遠處住了下來。這種現象俯拾即是,極爲常見。
這種人往往口頭上會說出諸如「我唯一依賴上師」這樣冠冕堂皇、漂亮動聽的言詞,實際行動中卻充分顯露出他對於如理如法依止上師根本毫無興趣的心態。一般而言,具有將上師視爲真佛的無僞清淨心確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但是我們如果能做到口中經常說上師就是真佛陀,心里也反反複複這樣觀想,夜以繼日對上師修清淨觀,那麽與上師越親近,對依止上師之道理的理解程度也相應會越來越提高。
還有些人顧慮重重地說:「因爲我心里對上師沒有信心、恭敬心與清淨心,如果獃在上師身邊,只能積累惡業而已。」這些人本來自己就已經不具有清淨觀,加之又不願意長期持久地修清淨觀,他們認爲反正我沒有清淨心,就順其自然吧,如此也是很快樂的,而不願意改正自己的惡行。(這些人純粹是破罐破摔、將錯就錯、自暴自棄、自甘墮落,孰不知無有清淨心也是可以改變的。如上所說,與具正信的道友相處,多觀想上師的功德,逐漸就會改過自新的,並且親近上師也有無量功德。)
有的人也滿不在乎地說:「既然對上師不能觀清淨心,那也是無所謂的,獨自住在偏僻的山里修法也是很好的。」你們對上師連一顆清淨心都不能觀想,那煞有介事地修法又能有甚麼利益呢?難道佛陀沒有說過大大小小的一切功德均依賴於上師嗎?而且,對上師能生起信心、觀清淨心的主因就是要在上師身邊住下來,隨後全神貫註聽聞依止上師的甚深竅訣,交往那些對上師觀清淨心的同修道友,與此同時對上師修清淨觀。大成就者事業金剛曾經請問金剛手菩薩:「生起信心之因是甚麼?」金剛手菩薩答言:「如若依止如第二佛陀般的上師便可生起信心;如果與具有正信的道友相處也可生起信心。」
也許有些人會有這樣的想法:住在與上師隔一定距離的寂靜山中,只要將上師觀想在頭頂上修清淨心就可以了,守在上師身旁又有甚麼必要呢?這種人也實屬愚昧無知、智慧淺薄之徒。如果不住在上師身邊,怎麽能聽受上師的講經說法?如果聽聞不到上師的講經說法,怎麽能斷除對教言的滿腹懷疑?如果沒有斷除對教言的滿腹懷疑,又怎麽能生起五道十地的功德?再說,如果我們要杜絕上師不歡喜的一切事情、對於上師歡喜之事盡力而爲的話,那麽住在與上師遙隔千里之外的地方怎麽會知道甚麼是上師歡喜的、甚麼是上師不歡喜的呢?如果說需要以三供養令師歡喜,無論是哪一種供養都必須親近上師才能做到。供養財物必須要面見上師前而供養;恭敬承侍也必須住在上師身邊,才能辦到;依教修行的供養也是同樣,要遣除修法的歧途障礙必須向上師請教,方能成就。
所以說,只有在上師身邊才能以這三種供養令師生喜。如若與上師遙遙相隔,那以三供養令上師歡喜就成了癡心妄想,根本是無法辦到的。
舍近求遠
當然了,如果自己與上師天各一方、遙不可及,或者上師已不在人間,在這種情況下因爲沒有真身的上師在前,我們不得不通過憶念觀想上師在頭頂或心間等處而修清淨心,並猛厲祈禱。可是現在自己本來與上師近在咫尺,有直接參見上師機會的此時,卻不對上師真身進行祈禱以求得加持,反而矯揉造作地將上師觀想在頭頂上來修持,這樣舍近求遠的做法又有何必要呢?即使是上師色身已離開人世,我們也要真切發願生生世世不離上師並誠摯祈禱賜予加持,那麽上師健在之時又怎敢輕意揚長而去呢?我們在多生累世中也難得有機緣幸遇如此賢德上師,如今幸運值遇一次,本應當像盲人抓住象尾片刻不放那樣,寸步不離、緊緊跟隨上師左右,可偏偏有些人就是不能穩重持久地安住,他們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也會斷然離開上師,到遙遠的地方去住,這種膽大妄爲之人難道不是鬼使神差、惡魔入心了嗎?
如果現在無有任何必要的情況下隨隨便便離開上師,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斷掉後世值遇上師的習氣緣分,良言規勸你不要故意積累使自己許多生世中都遇不到這樣能講經示道之上師的深重惡業。
如果自己能持之以恆長久親近上師,則可獲得廣大的利益。相反,如若做不到日久歲深地長期依止上師,那麽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的。正如《藍色手冊頌》中所說:「恆時不離依上師,成辦諸事片刻非。」《藍色手冊釋》中這樣寫道:「貴族的兩兄弟其一雖然智慧高超,並具有信心,卻因不親近上師而淪落成一位商人,最終慘遭橫死;另一人雖然既無信心也無智慧,但因親近上師而成了聞名遐邇的好修行人。如果能夠做到恆時不離、始終如一地親近上師,那麽就會像那若巴一樣相續中生起夢寐以求的一切功德。」
相形見絀
在當今時代,大多數人都認爲依止上師的目的就是聽受教言,因爲必須在聽聞教言的基礎上才能實地修行,所以應當首先在一年或幾個月當中依止上師,求得所有的教言後自己另找一處地方去修法,就可以了。有這種想法的人不乏其數,到處可見。
這些人求完教言後便像烏鴉銜著肉飛到別處去一樣不顧一切地跑到其他地方去實修了。可是,你這樣做根本無法得到任何加持,恐怕只是徒勞無益而已。仲敦巴格西在依止色尊者上師期間,對其精心承侍,甚至包括放牧、清掃人糞馬糞在內的事都盡心而做。後來拜見阿底峽尊者時,他心有疑慮地請問尊者:「先前我所做的善事中哪些最有意義?」尊者極爲肯定地說:「在你做過的所有善事中再沒有比你恭敬侍候色尊者上師更有意義的了。」如果以那若巴尊者依止帝洛巴上師、瑪爾巴尊者依止那若巴上師、米拉日巴尊者依止瑪爾巴上師那可歌可泣的事跡來衡量的話,現在的有些人從上師那里取得教言後,爲了上師竟然連身上出點汗水的苦行都不能做,自己只身一人去修行當然不可能生起任何功德了。前輩的大成就者們悉心畢力承侍上師,身語意付出了何等的代價,可以說是不惜粉身碎骨來積累福德資糧。
所以,三門不如理如法地令上師歡喜,反而隱居在另外的地方,僅僅憑著對教言的一知半解如何能生起功德,這樣做的人到底又是爲了甚麼呢?倘若像討債一樣從上師那里收取甚深的教言隨即便獨斷專行地到另一處去住,那麽請問你一開始依止上師時已經供養了身語意這又作何解釋呢?如果你自我作主的話,那上師還有甚麼權利可言?這麽說,原來你是在最初上師恩賜教言之前供養身語意,等教言已完全得到手中以後便強硬地奪了回來。這實在是罪大惡極的舉動。
令師生喜極重要
有些人根本未曾慎重觀察上師高不高興,一開始就心急如焚地對上師說:「希望上師盡快賜予我教言。」之後今天追著上師,明天也跟著上師,在一個月中就這樣糾纏不休,最後他終於如願以償,得受了完整的教言。但因爲上師是在無可奈何、心不歡喜、極不情願的情況下傳授的,所以這樣的教言不僅僅不能使他受益匪淺,反而會深受危害。從前有一個人在博朵瓦格西毫無情緒時求得了不動佛的修法,結果事隔不久他就一命嗚呼了。普穹瓦尊者對此表態說:「我認爲他的死完全是由於在格西心情不悅的情況下求法的緣故。」如《藍色手冊》中雲:「一切大乘之教規,令師歡喜最重要,上師極爲喜悅故,一切所爲具大義。相反教言雖具全,然彼不會得加持,故當努力令師喜。」
如果上師在滿心歡喜、心甘情願之下賜授教言,那麽所傳的教言即便是無頭無尾,也會得到巨大的加持;上師在心緒不佳的時候,所傳授給你的教言就算完整無缺、毫無錯謬,你也不會得到絲毫的加持。因此我們一方面要盡可能以三種方式令上師歡喜,與此同時就是爲了一兩句教言也需要月複一月、年複一年專心致志地聞受。如果一心只想盡快獲得教言,好去別的地方,這種惡心劣意只能斷送一切善根功德,對此我們應當時時刻刻謹慎提防,盡力避免。
我們爲了能夠得到前所未聞的教言,此前要慷慨供養珍貴的財物並且爲了侍奉上師,必須有粉身碎骨、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的忠誠。已經獲得了教言後爲報答上師的深恩厚德也能一如既往地供奉自己珍愛的財物,以不顧生命、粉身碎骨的精神承侍上師。如果首先做到了這一點,那麽再循序漸進修行教言,便可源源不斷地填充福德資糧,從而自相續毫無費力就可以生起善妙的功德。
掌握尺度
最初依止上師以三種供養如理如法令師歡喜,此後,自己在沒有達到對於美不勝收的妙欲、利養恭敬如同猛獸面前擺放青草一樣無動於衷絲毫不生世俗貪戀的境界之前,萬萬不可冒冒失失脫離上師與同修道友的群體。離開上師道友、獨自避隱山中的修行人,必須是猶如獅子一樣完全具有獨立自主之境界的人。
所謂的如日月般逍遙自在周游各處,並非是指在匆匆忙忙之中於上師前聞受教言後就像丟棄擦屁股的石頭一樣舍棄上師與同修道友而到處游走之義。它的意思是說,獨自住在寂靜處時因害怕受到欲妙的誘惑而不固定居於一地,也不執著任何一處,猶如日月執行般雲游。換句話說,像日月那樣周游的時間並非是指我們對妙欲利養心懷極大貪執、深受引誘的此時,而是指通過長期依止上師與道友斷除對教言的增益疑問,得到了真修實證的較高境界之時。到那時候即使一些大施主、大官員、大人物們對自己畢恭畢敬、頂禮膜拜,供養如天界的受用般令人眼花繚亂的財物,但自己卻能毫無貪執地拒絕,並能像見到不祥之噩兆一樣將這一切棄如敝屣瀟灑而去。在尚未達到如此高的境界卻如此而行,自己獨居一處,對於豐富多彩的財物以及眾星捧月般的尊敬愛戴貪執強烈、不知滿足,以此毀壞自相續,到那時不用說如日月般周游,甚至會淪落到我執大得連世間人也不如而在碌碌無爲中庸俗慘死的地步。
當前多數修行人由於依賴於某位大官員、大人物、大富翁提供豐厚的閉關資糧,仰仗這些達官顯貴得到名聞利養,於是非常內行地曲從這些人的情面、也善於運用虛僞狡猾詐現威儀的手段,口頭上也是巧言令色、甜言蜜語地恭維奉承,最終就會像耶哦的生平那樣白白地虛度了人生,這樣的修行者大有人在。如果這樣做,那就與博朵瓦格西所說的「依靠化緣過人生,知足少欲心安樂」完全背道而馳了。我們應當深深省察自己究竟有沒有如此荒廢光陰。作爲修行人的我們理應唯一憑借化緣來度過此生,否則,隨著利欲燻心、貪得無厭惡習的驅使,在居心叵測地妄加袒護施主情面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人生的旅途已走到了盡頭,這是多麽令人痛心的一幕啊!
真假舍事者
還有許多修行人不住在自己的家鄉,自命不凡地聲稱我是舍事修行者而來到異地他鄉的一處山洞里安住,接著便幾經周折地尋找很多熟悉的施主,他們怎麽算得上是真正的舍事修行者呢?
所謂的舍事修行者必須要做到已經徹首徹尾地斷除了對妙欲的貪執,與任何人素不相識,自己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受任何人控制擺布。假設一位施主突如其來,那暫時與他結成施主與應供處的關系也未嘗不可,但是達成長遠的協議說「我是應供處,你是施主」,這是萬萬使不得的。古代的賢德也曾說:「友人施主莫久約,鼻肉勿給任何人。」有了一位施主以後,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照顧情面之類的事上費功夫。自己完全被人所制約,做甚麼事都無法自主,只能聽人穿鼻、任人擺布了。因此,無論住在何處,如果利養越來越豐富,施主與熟人越來越多,那麽立即就要像小蟲被木棍兒觸碰頭部一樣急不可待地到其他無人察覺的另一寂靜處去。能夠將這些欲妙視爲怨敵而離開的根本前提,必須要對欲妙有深惡痛絕的強烈厭煩心。相續中尚未生起這樣的厭惡心之前,不可一時沖動而離開上師與同修道友的集體。
也有些自我標榜爲舍事修行者的人,哪里有上師他們就會去拜訪,哪里有寺廟他們都會去朝禮,就這樣在一邊乞討一邊四處流浪中走完了人生的历程。這種現象也是屢見不鮮。這些人也同樣稱不上是舍事者。
堪稱爲舍事者的修行人,必須在具備知足少欲功德的基礎上深深憶念死亡,也要具有這樣的緊迫感:甚至僅僅喝滿滿的一碗茶都覺得耽擱了太長時間,並且認爲自己如此空耗人生實在很不好,於是立刻精進實修,需要有如此迫不及待的心情。相反,經常游手好閑在城市與寺院等各處逛來逛去,一會兒住在這里,一會兒又跑到那里,一會兒吃吃喝喝,一會兒又信口胡說,長期始終就是在這樣散漫觀光中蹉跎歲月,貽誤時機,毫無實義地耗盡人生,而且心里對此沒有一絲一毫感受,那還有甚麼資格聲稱自己是一位修行人。這些人漂泊不定,沿途乞討,稱他們是果腹充饑的游覽朝拜者倒是恰如其分,而與舍事修行人的名稱實在有些大相徑庭,換句話說,太名不副實了。
真正的舍事修行人盡管需要乞食維生,但乞食的方式與前者卻截然不同,他們在城鄉中化緣到幾碗青稞,參著蕁麻、大黃而食用,僅僅勉強維持生命不致於死亡便可,穩定地住在寂靜聖地踏踏實實地修持。
在自相續沒有獲得對欲妙毫無貪戀的境界之前若能穩重地住在上師與同參道友的行列中,只是依靠化緣得來的生活物品以及僧眾分發的資具維生,無有供養財物的施主,自然也就不必卑躬屈膝地維護他們的情面,對未曾得到的財物不去刻意尋求,也不對已有的財物心不滿足了。三毒所生的多種罪惡也自然而然滅盡,所以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義。
平時要外出去化緣也要得到上師的開許,事先心里做好這樣的打算:此次外出不能超過十五天,如果化緣到這麽多的齋食,就可以解決這幾個月的生活問題。如若非要尋找勝過這許多倍的財物不可而外出幾個月,那麽善法相應也會在這麽久的時間里中斷。無論得到任何齋食財物,只要能維持身體就可以了。如果無有節制吃得過飽,則誠如經中所說「身體難以養育,且難以滿足」。因此應當竭力克制,盡可能依賴於粗衣淡飯,克勤克儉,易養易飽。
摘自索達吉堪布講解的《山法寶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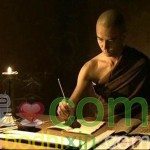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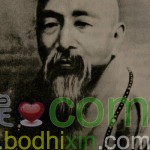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