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者,他將盡量地在「當下修行」,不會說要修行就一定要打坐,或者說要修行就一定要拿念珠,沒有念珠就好像覺得很不自在,沒有念珠就覺得好像沒有定力,一定要找一串念珠來念。所以只有他的修行已經慢慢的不被儀式,不被外在所限制了,他的修行已經慢慢地可以普遍到每一個空間,甚至他在大便的時候,他也在修行,因為他一直在增長他的涅槃,他在減輕他的輪回。所以他的空間就慢慢擴充到每一個地方,在吃飯,在聽經,在說話,在做事時都盡量地把他的心專註在動作上。
如果我的腦子散亂,就把心收回來。在看書的時候就定下來看,如果我有煩惱,就要知道是甚麼原因,是因為我不喜歡看這一段句子嗎?當我不喜歡看,就好像被逼得很苦,我會越看越煩。知道了這個原因,就會把這個原因舍掉,慢慢地放下,把心收回來。慢慢看,慢慢看;不要緊,不喜歡也得看。不是說:「很煩,不要看了,拿念珠比較好!」也不是說:「很煩,不要了,念經比較好!」他的心已經不會被這些形式所束縛,他已經慢慢地解脫了,他用甚麼都可以修行,看書也可以修行,聽也可以修行,吃東西也可以修行,喝茶也可以修行,說話也可以修行。所以他可以慢慢推廣,使他的涅槃一直地延續延續……
所以現在假如我們認清我們的道路,我們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涅槃,真正的苦、集、滅、道;假如我們還不清楚我們的道路,還有形式上的束縛的話,那就還很難修行。
我有時看到有一些人,我可憐他們。當他們做了一些事情而很煩的時候,就說:「去靜坐好了!」或者是聽一些話,很亂,很煩,就說:「不要說了!不要說了!」跑到房間去躲起來。這不是真正修行人解決事情的方法,應該是當很亂很煩的時候,就盡量地把他的心收回來,把心定下來,然後繼續做事。不是把自己關起來,這個還不是真正的修行人,還不是真正的有正見。
所以我們剛才要討論的八正道,最重要的是正見。我們若思考甚麼,就是透過我們的見解。我們會不喜歡別人,是因為我們的見解有污染,有邪見。我們對人家好,因為我們有慈悲的知見。我們做事,我們說話,甚麼都是從見解而來的。
比如說六祖惠能有「正見」,當他一聽到《金剛經》,他就開悟了。他有正見,他雖然不知道甚麼叫做正思、正語,但是我相信他在念頭上、在嘴巴上不會違背正思、正語。我相信,而且也肯定是這樣。雖然他在知識上也不知道正命是甚麼,但是在行動上,他卻是在正命之中。雖然他可能不知道知識上,或者理論上的正精進是甚麼:「已生之惡要把滅了,未生之惡就不給它生,已生之善就要把它增長,未生之善就要令它生起來。」這些理論上的精進,雖然六祖惠能可能不懂,但是我相信他就是這樣地在修。假如他沒有這樣地去修,那八個月的辛苦,他早就已經走了,哪還會得法證悟?如果是沒有正見的人,他一吃到苦,你說他會不會逃?他一定會不滿、厭惡:「來這裡都是吃苦,有甚麼好處,不如去找另一間寺廟比較好。」他就不會再待下去了嘛!可是因為他有正見,他知道修行是在於戒、定、慧。
我相信,理論上六祖惠能也不知道甚麼是正念,但是我肯定他在行為上,在修行上就是在正念之中,就是每一舉、每一動都在註意自己的起心動念,我肯定他是這樣。雖然他不知道正定是甚麼,不知道理論上正定有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但是肯定的,他在日常生活裡就是在正定之中,或者一定一直在培養,一直在訓練。
正見是見到甚麼呢?剛才已經說了,是見到苦、集、滅、道。所謂的「見到」,不是甚麼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那一些見,而是內心所感受的那一種「見到」、那一種的體驗,我們要體驗到苦、無常、輪回的原因就是貪愛、無明等等;而涅槃是沒有苦的狀態,它的道路就是保持正念,用真理來觀察。然後我們的心就平靜下來,就定下來,那個時候就是涅槃,有可能不是每一個時候都是在涅槃之中,但是我們已經體驗到了。(《你的煩惱熄滅了嗎?》連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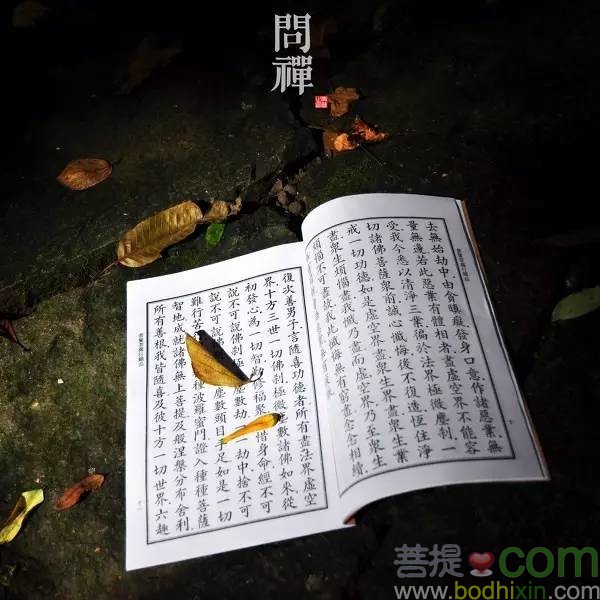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