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想知道「自我」是甚麼。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試著想了解為甚麼你們有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即使你想要理解你是誰,將會是一個無窮盡的試煉,而你將永遠看不到自己,你說打坐而沒有妄想是困難的,但是努力思索你是誰更加的困難——要達成一個結論幾乎不可能;如果你繼續嘗試,你會發瘋的,而且你不知道該對自我怎麼辦才好。
你們(西方)的文化,奠基於自我改善的觀點上。改善或改良的概念,其實相當具有科學性。在科學意識裡,改良的意思是,與其搭船到日本,現在你可以搭乘噴氣飛機。所以改良的基礎是比較性的價值,也是我們社會和經濟體系的基礎。我知道你們拒絕所謂文明的觀念,但是你們並不拒斥改良的觀念。你仍然想改進某些事,也許你們當中大多數人打坐是為了要改進你的坐禪。然而,佛教徒並不那麼強烈執持於要有所改良的觀點。
當你修習坐禪,試著要改善自己,你也許比較想要以心理學的方式來了解自己。心理學將能告訴你有關於自我的某些面向,但是它不能夠告訴你,你是誰。心理學只是就你的心做出多種闡釋中的一種。如果你去建議為心理學家或精神病學醫師,你會有關於自己無盡的新知識。只要一直去看醫生,或許感覺有點慰藉,覺得從所肩負的重擔裡被釋放開來。但在禪法中,我們理解自己之道於此大相徑庭。
洞山良價,中國曹洞宗創始者,曾說:不要嘗試客觀地看你自己。(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換句話說,不要嘗試去尋找有關於你自己,客觀事項只是知識訊息。他說,真的你,和你有的任何知識都非常不同。真的你不是那個樣子的。他又說到:我走自己的路,不管我到何處,皆與自己相晤(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
洞山駁斥你去攀執有關自我種種資訊的努力,並且說,須使用自己的兩條腿獨自前行。不管別人說些甚麼,你應該以自己的方式往前走,但同時,你也應與大眾一起共修。那是另一個重點。意思是,由於和眾人共修之故,你方能與自己相晤。
當你看見某人正認真修行著,你也同時看到自己,如果你被某人的修持深深打動,你也許會說,喔,她修的真好。那個她其實既不是她,也不是你,她的含義比那還多些。甚麼是她?仔細想了一會之後,你也許說。喔,她在那裡,而我在這裡。然而,在你被她的修行所觸動之際,她既非你,亦非她。當你被某事所打動時,那實際上是真正的呢。此處,我很遲疑的的用著這個字「你」,但是那個你,正是我們修行的純粹經驗。只要你仍在努力嘗試著要改進自己,你就有一個自我的核心觀點,那便是錯誤的修行,不是我們所意指的修行。
當你把心放空,當你放下一切,以一個開放的心態,只管修習坐禪。那麼不論你見到甚麼,皆與你自己相晤。那是「你」,超越了「她」、「他」、「它」或「我」。
只要你仍然執著於自我的觀念,費盡力氣要增進自己的修持,尋求某些事物,或試著創造出一個改良了的,更好的自我,那麼你的修行已經誤入歧途。你想要去達成那個目標,所以最終,你變得疲累不堪,而你要說,禪毫無用處。我打坐了十年,但是卻沒有的得到甚麼。
然而,如果你僅僅是前來這裡與誠摯的修行者一同共修,在他們之中發現自己,而你繼續那樣不間斷的修習下去,那就是我們的修行之道。無論你到甚麼地方,都能有這般體驗。正如洞山所說,不管我到何處,皆與自己相晤。若他看見水,那即是面見自己。見到水,對他而言,便已足夠,即使他不能看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所以了解自己的方法,並不是客觀地看待自己,或者從不同的管道收集資訊。如果人們認為你瘋瘋癲癲的,——是的,我瘋了。如果人們說你不是個好弟子,那也許沒錯,我雖不是一個好弟子,但我非常努力。那就夠了。當你以此態度來打坐時,你接受自己,並且接受每一件事。每當你卷入各種愚蠢的問題時,與你的問題一起打坐。在此時,那即是你。若你試著要逃離的你的問題和麻煩,便已經是錯誤的修行了。
若是你固守自己所制造的概念牢牢不放,像是一個自我的觀念或客觀地事實,你會失落在那個由心所幻造的客觀世界裡。你創造萬事,一件接著一件。無有止盡。也許你早做了各式各樣的世界,而且創造並觀看許多的事物是十分有趣的,但是你不應該迷失於創造物當中。
修行的另一個面向是,我們思想,我們行動。我們並不是盡力去變成一塊石頭,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我們的修行。與其被妄想心或想象、情緒的活動所奴役,我們不如以其真實的意義來思考。念頭來自於我們真正的自我,自我則涵蓋了一切事物。在我們想到樹林、小鳥、所有萬物之前,它們都在思想著;當它們思想時,或是呻吟,或是鳴唱——那是它們的念頭。我們沒有必要去想的更多。如果我們明見事物如其本來之面目,念頭已經在當處;這種純粹的念頭,是我們在修行中所有的念頭,因此之故,我們也一直有從一己之中解脫的自由。我們能夠看見事物如其本然,同時,亦能思想萬物。因為我們不固著於任何特定的思想標準,對我們來說,既無正確之道,亦無錯誤之道。(鈴木俊隆《禪的真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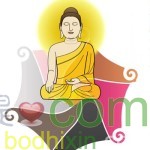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