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不僅是一個佛法原始精神的複興運動,同時也是一個更進一步的佛教現代化運動。換句話說,不僅是希望能「息邪說」而使世人明了佛法真正原本的精神——也就是「守成」,同時亦建立了新的方法和理論體系——也就是「開創」。能守成亦能開創,就是能深觀時代,順應時代而善巧地運用權教和實教。以我看,這就是一個人類古文化的現代化運動了。
今天我們如果想針對現代人類的問題與思潮,而揭開一個當今佛教現代化運動的序幕,我以為推動者若能把大乘看成一個過去的佛教現代化經驗,是會得到很多助益的。因為那一個時期菩薩們所建立的許多系統和糢型,到今天仍然適用。像權教與實教的靈活運用,勝義諦與世俗諦的開演,就是例子。如果我們不能由過去先賢曾走過的路吸取經驗而再往前進,人類的文化將永遠只停留在原點。而人類之所以有別於其他生物而能建立文明,也正是因為人類能由過去的教訓中累積經驗。
故在本章中,我想以佛教的現代化為立足點去看大乘佛教,看看有甚麼是那個時代的人早就已做過的,並探討那些東西到今天是否仍然適用。立足於這樣一個了解之下再談開創,也許會比較實際。以下是幾個我們所能見到大乘佛教的特色。
一、 佛法的普及化
這是大乘佛教的一個基本精神,也是一個弘法上新格局的開展。其主要的論點是佛教應以「大悲為上首」,打破過去只屬於一小撮「有根器的人」之局面,走向群眾。使佛法能普及開來,利益更多的人。
這個理念事實上本來就是佛陀立教的本懷。我們可以由原始教典中佛有講到在家人應如何禮六方,敦倫盡份,而看出佛法本來就可適用不同根性的眾生。只是在原始佛教時期,佛陀說法的當機者主要是比丘,都是一些專志修行的人,故原始教典中對出家人講的話就較多。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佛教始終是在所謂「修行人」的圈圈裡,一直無法普及。
等到大乘佛教興起,情況就不一樣了。當時的那些佛教現代化提倡者,顯然地認為佛法應該是有利益更多眾生的能力和使命的,而不應該只是被用在一小撮修行人或學院派的圈子裡。於是佛法就開始了一個不斷融合的過程,而和人類其他的文化相匯通。形成了一個洋洋大觀,更豐富,更開闊,也更能適應不同眾生根器的大乘佛教。
基於聖龍樹所提出的二諦(勝義諦和世俗諦)思想,及由之而生的權實互用弘教原則,大乘成了一個不斷演化的人類文化活動。最後到了中國,形成了具中國特色的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到了西藏,就形成了密宗。這些頗具影嚮力的佛教宗派,都是順應時代和文化而形成的人類文化偉業。
若綜觀這一個整體的大乘文化历史推演,我們可以說當初那些大菩薩的苦心沒有白費。大乘佛教的成就是卓越的。這一個整體的佛教現代化運動,至少轉動了人類五個大文化區,利益的人何止百千萬億?今天的藏密和中國及日本禪宗的影嚮力,仍在歐洲、美洲及全世界發展著,激蕩著人類的思想和生命。而整個的中國佛教,可以說正是這一個偉大的佛教現代化運動的受益者。作為今天的中國佛教徒,我們實在是應該秉承著這一個偉大的人類文化傳統,而繼續往這一個佛教普及化的方向努力的。
今天不少研究原始教典的學人,頗對中國傳統佛教中一些較偏向宗教或儀式的東西不以為然,認為就是因為這些,佛教才逐漸衰敗變質。這個看法正確嗎?我以為值得深思。這些東西至少有一點,和大乘也和原始佛教的精神相應,就是慈悲地滿足了世人的宗教需要。佛法的本質雖然不是宗教,但佛法絕對尊重這世界上的一切宗教,也不會主動地去反對宗教,除非這個宗教對世人有害。大乘佛教反而更主動地把宗教情感融入佛法,方便善巧地一方面滿足了世人的宗教需求,另一方面又建立了權教,而使修學者能逐漸增上。這一種能迂回也能正直,在權變中又不失去立場的精神,正是大乘佛教「不舍眾生」的慈悲表現。
故在大乘佛教中往往有很多事好像看似很矛盾,其實這卻正是大乘偉大的地方。能拜佛,亦能把佛像當柴燒;能講「輪回」,亦能講一切法無我;能贊嘆一切有為功德,亦說離相無念是名真功德。這一切的一切,事實上皆是由大乘教的「權實互用」流變出來的。故菩薩行講究的離相無著,不但是方便教不著,就是究竟教亦不著。真正了悟的菩薩,是觀權教與實教等,佛與眾生等,淨土與穢土等。故能舍淨土而無怨,在世上與眾生「利行」、「同事」。故我以為若真探究到大乘教的深處,那真是開闊廣大的「人間佛教」。菩薩一切皆以眾生為著眼點,而決定該如何施設眼前的教法,並不堅持正法一定要怎麼樣。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所謂「廣開方便門」。但其目的是一樣的,即使眾生畢竟能見正法而得法益。
當然,為了普及佛法而廣開方便門地運用權教和實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也正因為不容易,故大乘佛教的發展,有時會產生一些偏差。但在整體上而言,局部性的偏差仍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因為的確有更多的眾生得到法益。我也希望近代中國有志於弘法的同修能有這樣一個認識,就不會在忽起忽伏亂象叢生的中國佛教環境中感到太沮喪失望。以大乘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永遠都是亂的,外道也永遠都是存在的。一個人想自求清淨,相對而言當然是容易多了。但菩薩道卻偏偏不這樣。大乘佛教主張菩薩永遠應走入紅塵,和眾生在一起,用合乎眾生根性的方法使他們覺醒而悟入正法。故在一個菩薩行者的生命中,他所面對的當然是眾生數不盡的不安、煩惱、猜忌與仇怨。他要普及佛教,就必須要承擔這一切。而他的智慧如果不夠深廣,當然就有可能會犯錯誤。
但在大乘教中有另一個教義,就是菩薩不怕犯錯。因為他所要做的事,幾乎已註定了他會犯錯。犯錯沒有關系,重要的是要知錯能改。故在菩薩的修學過程中,「柔軟」是一個很重要的修行品德,其意義就在於菩薩不會堅持己見,隨時準備接受其他更深刻的智慧。而菩薩的修行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也就是為眾生,為了正法,他沒有甚麼自己的東西好堅持的。只要這個「菩提心」猶在,再大的錯都不會徹底地毀了一個菩薩的「法的生命」,他都有再向上而利益眾生的機會。
我常會嘆服於當初大乘菩薩道立教者智慧的深廣,「菩提心」的施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它真可說是畫龍點睛似地,把菩薩道的神韻點出來了。的確,為了正法的普及和利益更多的眾生,菩薩吃一些苦,受一些挫折,甚至犯一些錯,都仍是值得的,只要他的「菩提心」沒有失落。只要他在一切的苦痛、挫折和錯誤後,仍有一顆向上向善為眾生服務的心,他就仍是菩薩。哪怕在世間的立場而言,他的處境已是再卑微不堪,大乘教的正義皆是如此。由此也就更可看出當初那些大乘教的立教者,不但不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反而是如實了解人性和世間的實際社會工作者。經中每會有「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如來善付囑諸菩薩」的敘述,其背後所真正蘊涵的智慧與感情,恐怕不是用世間的語言文字能充分表達的。
總而言之,是大乘佛教想盡辦法要使佛法能打入社會的各階層,融入人類的各文化,使佛法能更普及。這個意圖及成就,應該是可被我們肯定及贊嘆的。我希望將來的佛教現代化,要能延續這一個傳統,不要倒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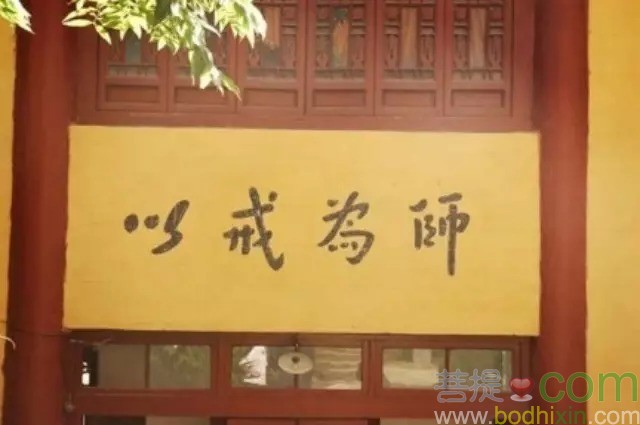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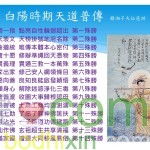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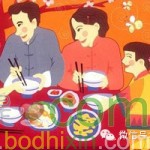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