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形式的動物,文化則是內涵透過形式表現在外的連續相。一道菜是一個形式,一種文體也是:一種風俗是形式,一個特定的行為糢式也是。而無論是一道菜或一種風俗,只要連續地出現在現象界一段時間,它就構成一個「文化」或「次文化」,同時也就是一個內涵的全部或部分展現。
所謂「一個內涵」或「一個文化」,只是相對應於一個形式的方便說法。而事實上「質」上的東西是無法分割或單獨存在的。例如我們說「非洲文化」,只是一個相對幹某個形式(「非洲」為一地理的形式)的方便說法,來表示和一個地域範疇相關的內涵。事實上那個內涵本身是無所謂非洲的或亞洲的,原始的或精煉的。它只是它。只是若不透過形式,我們很難表達思想。故人類透過各種形式來表達思想及內涵,就有了所謂的文化。
人類無法離開形式而單獨存在,而人類存在的本身也是內在的形式表現。
修行要憑藉形式,正如人無法離開形式而存在一樣。故佛在世時曾多次地呵責自毀肢體而欲修道者為愚人;也反複地提出「人身難得」的思想,向修行人指出修行必須仰仗有形的「人身」。正因為佛陀早巳證得實相,早已悟出了「性相不二」的道理,並徹底地看出了部分修行人以為離開「相」而別有「性」的謬見,故佛把這一種思想清楚地指為偏激的二邊之一——常見。明白地對學人開示這一種思想是不正確的,不會有利益的,也不會成功地令修行人達到目的。以為現實人生中的東西為不淨,而欲脫離或舍棄這些,為佛在世時印度本土頗為流行的思想。當時的印度人對整個「人類存有」的形式是頗為不耐而厭倦的。他們想擺脫掉形式,排除掉形體。這種心態頗能為當時人的一種宇宙觀——欲界、色界、無色界——表現出來。他們認為真正最高級的存在是連「形式」都沒有的,乃至到一種「無所有處」及「非想非非想處」。
佛陀在證果後,清楚地看出了當時印度人的迷夢。但為了要隨順眾生的根性,故佛也慈悲地講這些當時印度人朝思暮想的東西。但講來講去,佛仍沒有離開一個開悟的世間導師的立場。他屢次向學人表示,無論你修到再高層次的「定」,「色界」也好,「無色界」也好,凡是「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中的東西,就是因緣所生的,也就是所謂的「有為法」,皆是不安穩,不可依靠的。無論是大小乘經,這一個佛說的基本立場均沒有改變。《金剛經》中所說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及《法華經》中的「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就是最好的例證。
佛最主要欲向修行人指出的,並不是在三界之外別有一「第四界」或第五界」,才是真正最究竟、最高級的存在。佛是在徹底地對當時修行人的這一種想要擺脫掉「形式」的思想作批評,指出這一種想法為甚麼不合乎緣起法則,及由其而衍生出之修行為甚麼不合乎中道。
想要完全擺脫掉形式的思想,事實上頗為普遍地存在於許多的宗教與形上學體系裡。這種思想簡而言之就是「厭世」的思想,其根源是人對生命及世間的不滿足,乃至失望甚至絕望。人一旦有了這一種思想,整個的生命和人格就變成「不在當下」了。會成天滿腦子都是那一個不在世間的存在。他就算能把身念處修好,做到語默動靜都覺察到自己的身體和動作,但你若仔細地觀察他整個的人,會發現他真正的人是在「另一個地方」。他也吃飯,也說話,也會笑,也走路,但整個的人格裡有一種「恍惚」的氣質,眼睛裡有一種異樣的光彩。仿佛在說:「這一切都無所謂,只是暫時的。重要的是……」
這一種人並不會真正地關心世上的甚麼事情。他並不「存在」在這個世間。你要他去「選舉投票」或去參加公共聽證會,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他也不會去參與環境保護、支持民權、愛護動物等活動。他如果去參加了,也只是因為那些活動支持他的厭世形上學思想。故修四念處為甚麼一定要修到法念處的層次,在此就十分清楚了。當時和佛同時代的那些修行人,不少人的身念處、受念處及心念處可以說都修得很好了,差的就是沒看出自己生命深處的厭世思想。故舍利佛一聽到有人提到「因緣法」,馬上就證果,原因就在這裡。因為畢竟佛法講的是一個人生命徹骨徹髓全面的覺醒。佛陀也正因為這個全面的覺醒,才被人尊稱為「正等正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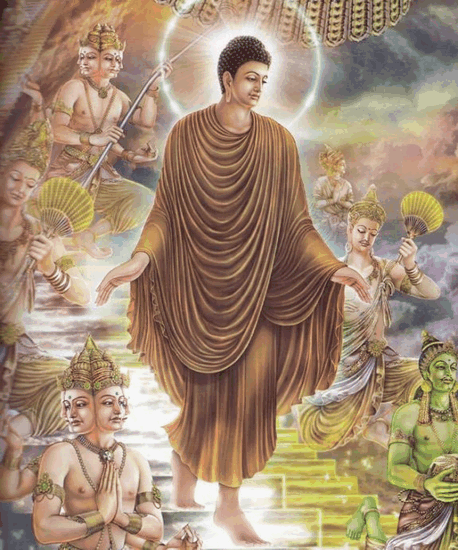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