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念處主要修行的重點是非常「科學的」,即欲解除苦惱必需隨順著形成苦惱的「緣」去下工夫。這其中包括找出甚麼是「苦」,找出甚麼是「苦」,找出甚麼是「苦之因緣」,了解及認識「苦之因緣及其性質」,進而在日常生活的四念處中練習自我離執力,轉變那些形成苦的因緣。
這就好像一棟房子失火了,有人用水或沙去救火一樣。其人進了房內,一定要用眼睛看,找出甚麼地方有火,再用水或沙去止住火勢,才能達到滅火的目的。苦其人連看也不看,只是一味地用水亂潑,則水很快就用完了,而火卻越燒越大。故「看出來」(即找出問題及其原因)是絕對必須的,是救火的開始,也是修行的開始。
念要能活用,不能念死書。學佛法也是要能運用,並不是「科學應考」。人若會講緣起,但不會找出自己苦惱的「緣」的話,縱能把整本佛經倒背如流,又有何用?
「看出」一件事和「接受」一件事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佛要我們看出自己的苦惱和苦惱的原因,卻並未要我們無條件地接受任何事情。「看出」一個事實是「智慧」,其價值是無法為任何其他東西所取代的。只是一味地「接受」他人的意見,哪怕是再好再對的意見,都不能算是跨出了止息苦惱的第一步。
最怕的是許多人念過許多類似基督教《教理問答》之類的佛書,能作出許多「止息憂悲苦惱」之類的回答。你問他眾生為何有苦,他能講出一大堆佛學語句,又是無明,又是貪瞋癡,又是「二邊」等等,對答如流,但其人對這些事和自己有無關系卻不甚了了。他認為自己已懂得佛法,差的僅是「修」了。於是終日念經持咒,到最後一無所成,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他連自己有何苦惱都弄不清,當然不可能看到自己的「無明」、自己的「念瞋癡」或自己的「二邊」。連看到都沒有看到,還談甚麼修?修甚麼?終日忙了半天,連自己在做甚麼都不知道。高談「了生死」、「解脫道」,只是在做夢罷了。
各位不要以為我在危言聳聽,故作驚人之語,我講的正是今日許多學佛人的真實情況。我以為如看《教理問答》的人不能藉書中的內容增進對自我的省察和了解,還不如不看。
智慧不僅不能為接受知識所取代,也不能為「德行」、「謙虛」所取代。有一等人不但會說佛法的知識,其德行也是非常好,一點貢高我慢都沒有。見人就說自己「業障深重」,處處都說自己甚麼都不懂,這種人當然要比我慢心高的人好多了。但他如只是有一種謙虛的心態成了習慣,卻並沒有真正看到自己甚麼地方「業障深重」,為何「業障深重」,這人只是一個「謙虛成性」的人,和自己苦惱的止息沒有直接的關系。無法解決自己苦惱的人,縱是謙虛有德,仍無法幫助其他的人解除苦惱。
「業障思想」事實上後來在許多人的了解中形成了一種有偏差的緣起思想,和「宿命論」相似,而成為修行上的障礙。所謂有偏差,就是當修行人在觀察生命的時候,只見到了其中部分的緣起性,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部分。通常有這一種想法的人,總覺得佛教既然講緣起,故生命中一切的事均是緣起而有因果性的。就對人生抱著一種表面上頗為豁達,但事實上卻非常消極的人生態度,以為生命的一切均早已被一樣看不見但卻非常實在而又無以回避的東西決定了。不少佛教徒就說這一樣東西叫作「業力」,而非佛教徒就說這是命運。這一種思想發展到極致時會成為百分之百的宿命論,以為一個人無論做甚麼或想甚麼,事實皆是枉然。你是修行也好,不修行也好,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其結果都是一樣。
我時常說這一種思想就好像一個只有一只眼睛、一只手和一只腳的人。因為這種心態只是往生命中的過去看,開口閉口就說「宿緣」、前世,卻不看未來。因為只往過去看,故當然覺得現在種種均為過去所決定。但未來種種是不是也同樣地將由過去再加上一段時間的未來而決定呢?而那一段時間尚未發生,是將會因為我們的努力而有不同的。我們如果只是一味地往過去看,會變得不夠積極而造成一種無力的心態,就好像一個人只有一只手一只腳一樣,做甚麼事皆是半調子,也做不了太多的事。事實上是他的生命能力已完全被他有偏差的「宿世緣起觀」所決定了。他只有一只眼睛,只往過去看,故他永遠體會不到「現在」的價值。他不知道把握現在,只是讓時間一秒一秒、一年一年地流逝掉,讓其成為「過去」。然後再在「現在」搖頭嘆息說:「一切都早已註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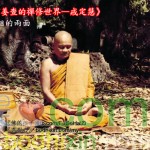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