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間生命觀的透視
大千世界,每個生命都免不了終結的一天。「生從何來,死往何去」,成了人類历史上的永恆話題。人們分別從哲學、文學、藝術、宗教、科學等不同領域,提出了異彩紛呈的答案。這裡,將其主流歸納為神本、人本、物本、我本四種生命觀。
神本的生命觀,認為有一個無始終、無內外的宇宙創造者及主宰生命的上帝,以西方基督教最為顯著。他們認為上帝是生命存在的本源,並創造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進而繁衍出人類,同時認為人的一生是贖罪的過程。奧古斯丁曾說:「(天主)負擔了我們的死亡,用他充沛的生命消毀了死亡,用雷霆般的聲音呼喊我們回到他身邊,到他神祕的聖殿中。」告訴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僅為請上帝諒解,從而回到他的懷抱。這在整個西方中世紀,成為一般人的生命觀。
人本的生命觀,對於人從何而生、人的特徵是甚麼,依據人類通常的認識,以為生則稟之父母,死則歸之天地,除此以外的無須推究。孔子曾在回答生命問題時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強調了對生的本質認識,是明白生命的關鍵。對於生命價值的意義,孔子則認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法家的荀子也說:「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矣,不可以生而可以死矣。」強調了生對人的重要作用,先知生,才能明白死的道理。可以說,這些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本生命認識的主流觀念。西方在文藝複興以後,也漸漸從神本的生命觀中獨立出來,強調「天賦人權」,主張人生而平等。但丁就曾說:「人的高貴,就其許許多多的成果而言,超過了天使的高貴,雖然天使的高貴,就其統一性而言,是更神聖的。」這是從主張人的創造性、主動性方面,對生命的有限詮釋。但他們大多承認天命,對生命何來何去則談得很少,可以說是對神本生命觀不徹底的反對。
物本的生命觀,從物質的構成層面來解讀生命現象,包括物質、物種、物類三個層面的內容。西方唯物論哲學和近代生物學、醫學、心理學即側重於這種生命觀。亞裡斯多德曾說:「整個靈魂在人死後繼續存在是不可能的。」他認為生命的形式與質料是統一的,具有共在性,人的生命結束後,只能靠同類子孫作為種族的延續存在下去。奧地利著名生物學家貝塔朗菲也認為,生命表現為無數種植物和動物的形態。生命活動的過程,是生物在其組成的物質和能量連續交換中保持自身,它能以活動的方式對外界的影嚮作出反應。與此同時,他也承認生物學只能陳述其表徵或某種規律。也就是說,雖然我們已掌握了某類生命的基因,並可進行體外的人工繁殖,但絕不意味著我們掌握了生命本質的全部,因為生命特別是人的生命還有意識、情感、思維等豐富的精神內涵。而作為心理學家的弗洛伊德,則認為生命是「本能」決定的。現代醫學對生命的認識,更側重從呼吸、血液循環、大腦活動、心髒起博等方面來觀察生命現象。這些說法,基本上是以現有生命為對象而作出的結論。他們一般都受到近代生物進化論和唯物論的影嚮,只承認生命是「自然演化」,其存在「只此一身」,無有前後。
我本的生命觀,則重視自我的作用,即以生命意志、自由意志為主。莊子曾說:「乘萬化而未始有極,樂不勝計;或謂:物各有一太極,人各有一天地。」不承認有創造宇宙的神,為我本生命觀的代表。西方近現代哲學家叔本華也曾說:「生命本身就是滿布暗礁和漩渦的海洋。人是最小心翼翼地、千方百計避開這些暗礁和漩渦,盡管他知道自己即令历盡艱辛,使出『全身解數』而成功地繞過去了,他也正是由此一步一步接近那最後的、整個的、不可避免的船沉海底,並且是直對著這結果駛去,對著死亡駛去。」接著,在尼採「上帝死了」的呼聲中,把人類帶進了以生命意志為特點的我本生命觀的世界。
從佛教緣起論的角度來看,上述看法自有他們的長處,但也有其局限。在佛教而言,人只是六道中的一類,並不代表全部的生命現象。生命是由五蘊構成,其中沒有不變的物質存在,又不同於物本的認識。同時,生命是因與緣和合作用的現象,沒有不變的真我存在,所以非神本。而「我」也是精神與物質構成的暫時生命現象,也無不變的「我」。對此,太虛大師也曾從人生觀角度分析說,這樣的認識「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為人間的安樂計,則人本的、神本的人生觀為較可;為理性的真實計,則物本的、我本的人生觀較可」。這四種觀點,對於生命的認識皆有一定啓發作用,但須有抉擇地進行甄別。因為生命現象十分複雜,一般人僅能從個人有限的知識和理性出發去認識,所以產生了許多困惑。有些人在錯誤生命觀的影嚮下,不惜傷害他人生命,做出對社會、對人類不利的事情;也有人因此追求物質至上,信奉享樂主義、拜金主義;還有人形成了個人主義、虛無主義的生命觀,由此走向狂妄自大或消極自棄的人生歧途。佛教認為,對於生命的正確認識,從社會的角度而言,關系到人類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重大問題;從個人方面說,也涉及個體生命能否發揮自身積極作用,獲得智慧,得到從痛苦中解脫的幸福。以下,我想從佛教對生命的啓示,來談談生命的意義。
二、佛教生命觀的本質
佛教生命觀揭示,現存生命以五蘊(色、受、想、行、識)和合為特徵,精神(受、想、行、識)與物質(色)的互動,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條件。當五蘊離散時,並沒有一個常存不變的真我存在,而以業識的形式流轉,這是它與有神宗教的區別所在。如佛陀所說:「諸比丘!色有故,色事起,色系著,色見我,令眾生無明所蓋,愛系其首,長道驅馳,生死輪回,生死流轉;受、想、行、識亦複如是。」當我們執著物質的身體或精神是我,就構成生死流轉的動因。佛教認為,在生命自生至死的持續過程中,由壽(生命存在所依的物質部分)、暖(體溫)與識(精神)和合,為其存在形式。壽維持暖與識;暖與識亦維持著壽,三者相互依存以延續生命,此時的生命被稱為「本有」。當一期生命臨終時,壽、暖、識分散,執持生命的識與肉體脫離,就從本有進入死有狀態。而此期生命結束,到再次投生前的存在叫做中有。下一次的投生則為生有。
在生命流轉中,推動其不斷投生的就是業力,這是有情以前善惡行為所積存下來的力量。在無常無我的身心活動中,生命是不常不斷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雖已過去,但並不等於沒有,它轉化為動能而不失。等到現有生命變壞時,存在的動能──業力,就引發並形成新的身心活動。此依業而有的流轉,並無主體的我,也不是現存生命體上所顯示的假我(此指世間一般人所稱我的代名,佛教並不否認它的暫時存在)。佛陀曾說:「有一種見,如是如是說:命則是身;複有如是見:命異身異;又作是說:色(受、想、行、識)是我,無二無異,長存不變。」這也是佛教對印度當時「真我輪回說」的批駁,從而形成佛教生命觀的特質。
關於生命如何流轉,佛教以「緣起論」為其本質;以十二「緣生法」作為流轉過程的詮釋。佛陀曾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說明生命現象以無明(長久積累的煩惱與業)為始,以行(造作諸業)為助緣,從而形成新的生命(識);業識投胎之後,與肉體和合而成名色(只有胎形);到胎兒長成眼等六根成人形時為六入。出生之後,因為與外在環境的接觸(觸),而生起種種感受(受),並對感受產生苦樂分別而有愛欲生起(愛)。又因對愛執著不舍,而有追求之行為(取),由此生成新的業因,招感未來果報(有)。接著,有將來五蘊和合之生命體(生)的產生,並有新的生死(老死)。以上十二支,以起惑、造業、受生三個層次,說明生命的延續過程,並生成緣起的、周而複始的因果鏈。
但是,佛教的緣起生命觀,並不以說明生命的流轉過程為滿足。佛陀更告誡弟子們要正見緣起,不能於此產生執著:「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知善見,不求前際(前生),言:我過去世若有若無,我過去世何等類,我過去世何如;不求後際(後世),我於當來世為有,為無?」我們必須於「因緣法、緣生法,如實正知,善見善覺,善修善入」,不在過、未兩世的理論說明上糾纏,才能最終解脫生死,不為煩惱痛苦所逼,這是佛教生命觀的重要特徵。

三、佛教生命觀的特點
由佛教「緣起」的生命觀為基礎,我們可以深入發掘出佛教生命觀的諸多特點,如珍視人生、生命平等、趨善進化、終極解脫等。這為當代人應如何認識自己及一切生命現象指明了道路;為樹立新的人生觀、價值觀找到了契機。
佛教生命觀要求我們珍視人生。在緣起的生命觀中,個體生命由於所造善惡業的差別,故招感不同的果報。佛教以六道來說明生命的存在形式,即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天。生命就在此六道中,不停地生此死彼,了無出期。人生在六道中的特勝,印順法師曾進行了總結。一、從所處的環境說,生在三惡道的眾生,因所受苦難太深且沒有間歇,所以無暇旁顧,更何況修學佛法;阿修羅道因嗔心太重,一生大多數時間都在與天爭鬥,沒有時間學習善法;天道則因各種誘人欲望太多,只顧享樂去了,所以也沒有時間修行。只有人間苦樂參半,所以能知苦、厭苦,常思從痛苦中脫離出來。二、從心行上說,與其它生命比較,人類具有慚愧之心,能由此止惡行善。三、從智慧上說,三惡道眾生少有智慧,只有人類能運用思維去改善生存環境,並通過修行證得出世智慧。四、從精神上講,人類有堅強的意志,能克服困難、忍受種種逆境而實現目標。總之,人道的殊勝非其它生命所能比,所以佛教非常重視人生的作用。佛陀曾將人生的珍貴比喻為:「盲龜浮木,雖複差違,或複相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暫複人身,甚難於彼。」人生之難得,比瞎眼烏龜碰到飄浮於大海中的木頭上的孔還要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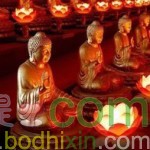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