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了義的佛法,只能度人格完整有生命力的心靈。中國禪宗的祖師,曾用過尖刻的言辭來形容只知躲在自我的牢籠裡執迷不悟的人,說這些人是———趕屍漢!
禪宗的話雖然平易通俗,但也蘊涵著深刻的修行體驗。
甚麼是趕屍漢?哪一種人是趕屍漢?他們又為何會被祖師斥為趕屍漢呢?
中國人有句話說:「天生我才必有用。」依我看,能善於運用自己的生命以饒益眾生的人,就不是趕屍漢。而不願運用生命,發揮才能,把力量投入法界者,這種人雖在,卻等同不在。只是在吃飯、睡覺、浪費陽光、空氣與水。這種人不是「趕屍漢」,又是甚麼呢?
過去傳統中國人的觀念,總以為富貴是福。一個人一旦有錢有勢,就可一呼百諾,甚麼事都不用做。整天都有人伺候著、哄著,捧著。而富貴的人所做的,不外就是串串門子嗑磕牙,打個小牌聽聽戲。當一個民族的生命價值取向,是在往這一種「懶人哲學」的道路上前進時,這一個民族怎麼會有發展的前途,又怎麼能有圖強的活力?
健康的文化生命觀
故若真地去探討佛教的生死觀,我以為到最後,必然會發現生命觀其實是每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一個民族若能有健康的生命觀,就能使民族及文化的發展有充滿生機的導向,反之則會使民族走向衰亡。正確地去了解並詮釋儒家、佛家及道家的生命觀,使它們能為中華民族這一個有悠久历史文化的生命之河,註入新的生命力,當是今天所有華人文化工作者的責任。
而站在複興根本佛法生命觀的立場,我就要指出除了懶及逃避、怯懦外,「執著」事實上亦就是生命之死。這一點,可能和一般人所想象的相反。
生命之河若沒有太多執著,河水原是清澈見底的,充滿活潑的生機與生趣。
而河水之所以能明澈見底,正是因為它流暢而無所著。不會因兩岸的景物別有一番風光而不肯往前流,也不會因眷戀兩岸的景物而卷走河邊的泥沙。
但一旦生命之河失去了本然的天真而「執著」起來,則原本明澈的風貌就要改變了。河流一旦想「帶走」一點甚麼,則河水就混濁了。而一旦執著到連流都不想再流的地步時,河就要成為死水了,也就會生滿水藻與小蟲。此時的河當然就是死了。而使生命之河的流動受阻的執著,在佛法中我們可概括性地分為貪、瞋、癡。而它們每一樣都能使生命「真正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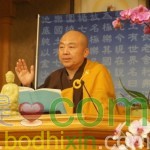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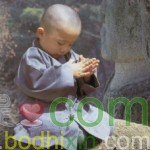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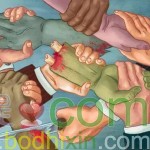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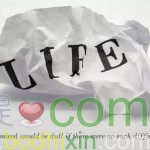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