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章中我們討論過了「唯心論」及因其影嚮而造成的一些不重形式的性格及修行心態。通常這一種心態一旦形成,往往就會造成人們一種「不在當下」,甚至「不在世間」的個性。身體雖在此處,但心總是在一個遙遠微妙的地方。但無論「那個地方」是多麼微妙的,以四諦及四念處的修行立場看,均是障道因。修行人皆當看清、遠離。
也許正因為「部派佛教」後來的發展有越來越往「內」的唯心趨勢,使修行人越來越不重世間,故一群有見識的宗教改革家才會提出了重新肯定世間的「大乘思想」。並提出以「六度」等和生活直接相應的理念為主題的修行,使修行人能逐漸遠離褊狹的唯心論修行的缺失,而能把註意力放在當下的世間。如果我的假想是正確的,則近代不少站在「原始佛教」立場而完全否定了「大乘佛教」的人,就該重新思索大乘思想的本質及其和原始佛教的關系了。
我相信當初大乘思想的倡導者們,是因為見到佛教整體的發展已越來越遠離了佛教的基本精神,才出來作佛教複興的工作的。從許多地方可以看出當時那些複興工作者用心的良苦。重新把修行由唯心思想帶回世間,也只是其中的一面。故以我對佛法的了解看來,不但不會覺得大乘思想是對原始佛教的反動,反而覺得大乘在本質上是很接近原始佛教的,只是後來因為發展的年代久遠;所謂「大乘」也逐漸變質了。像當初大乘思想所批判的唯心思想,也又重新回到了大乘之中。但如果有人看到了大乘後期的現象,就全盤否定了大乘,就和有人用部派佛教後期的現象否定了原始佛教一樣,是不公平也是不正確的。
我之所以要講這些,是希望大家在研究佛教及修學四念處時,能徹底地擺脫宗派與門戶之見的束縛,直觀人生而不再在古老的問題上打轉。對一切佛教的問題均是可以反省、討論及研究的,但沒有必要再去「打倒大乘」或「打倒小乘」了。凡是修學四念處者,均應有「如實觀」的修行素養,而能遠離一切的「大小乘見」。事實上平心而論,今天又有哪一個宗派,哪一個團體能完全代表當初的大乘呢?而又有哪一個國家,哪—個地域的佛教徒敢說他們所傳承的佛法就是最原始的佛教呢?在兩千年後的今天,如果還有人在攻擊「大乘」或「小乘」,以我看不但是史識不足的表現,反而更讓人覺得是「過時」甚至「過氣」了。
本章我想要研究的,並非佛教史上大小乘對立的問題。我的主題是接著前章唯心論的探討後,希望能進一步地再探討修行中對「性」與「相」的另一個偏執——也就是對「形式」的偏執,並分析其對修行的影嚮。
四念處的修行,精神上該是合乎中道的,既不偏重內涵,也不流於形式。偏重內涵的修行,容易有唯心論的傾向,其缺點和影嚮我們已在前章中討論過了;而偏重形式的修行心態,不可否認的也已在佛教發展的後期形成了。我希望在本章中能分析並批評流於「形式主義」的修行,進一步讓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四念處修行的旨要。
我在前章中曾指出人是形式的動物,而修行也不能離開形式,故「形式」當然是重要的。從修行人的身體、環境,到整個的教法,都是其修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形式。但同時修行人也不可忘的,就是形式固然重要,但修行絕不「只是形式」。
《金剛經》中佛所說的四句偈「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正是經典中對「形式主義」的修行最有力的批評。近代已有若幹新興的佛教宗派在強調某一種「聲音」,甚至某一種音波的震動,就包含了全部的佛法。於是把所有的精神皆耗在發出那一種聲音上。這正是形式主義的修行發展到了極至的表現。而通常這一類型的形式主義修行思想,大半皆有極濃的神祕傾向。
當然,一般的佛教徒還不至於如此偏激地以為某一種「音波」就真的能貫穿佛教的整體。但程度上沒有如此之甚而本質上很接近的思想,是不是也存在於傳統佛教中呢?以我看不但有,而且還不只一端呢!
最明顯的就是一種流於形式的「功德思想」,普遍地存在於傳統佛教中而成為修行人很本能的一種心態,使得許多人以為「某一件事」或「某一種行為」就必然是有「功德」的。於是對這些有功德思想心態的人而言,人生就像是算一本「功德錄」上的總帳。這種人的修行會成為斤斤計較的「執相」,而不能發揮佛法中不離形式但也不即形式的中道,是很可以理解的。
這種思想表現在修行上,就造成一種以「業」為主要對象的修行觀念。不少修行人修行的主要內容就是「消業」。這種態度最嚴重的缺點就是不夠直接。因為不直接,也就不夠有力。四諦講的修行態度,是以人生中之煩惱一也就是「苦」——為直接對象的,而不是以任何思想或概念。故四諦修行的方法論鼓勵人用洞察力去直觀苦及苦因,而不鼓勵人直接去觀察「業」。
「業」並不是不存在,但它是一個較「苦」更抽象的東西,而且更概念化。修行人可以很直接地觀察「身」及「心」上的苦,但要人觀察身及心上的「業」,就仿佛隔了一層甚麼,沒有那麼直接。故修行人若以四念處去觀照身及心的一個「苦」,他是可以很明確地知道那個苦的升起及落下的種種情形,而清楚地知道修行在每一個狀況下自己當如何拿捏。但要修行人借著拜佛、念佛或唱念而「消業」,就沒有那麼直接了,也很少有人能明確地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消業了,或至少消到了甚麼程度。大多數人皆是先採取了一種類似基督教徒「我是罪人」的思想,認為自己業障深重.然後再用許多方法來消它。但到底消了沒有,卻缺乏一個有力的修行生命中的體驗來驗證它。結果是許多人消了一輩子的「業」,卻沒有能改掉自己的一些不良習慣。以此而說,這是因為佛教整體地忽略了直觀人生的四諦及四念處,卻用了一些比較偏重抽象觀念及形式的修行而造成的現象,我以為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事實上形式如果離開了內涵,還能在整個因果流轉的過程中有多少作用,是不難想象的。同樣的一個布施的行為,有人做了是慈悲,而有人做了就可能是貪圖名利。布施者如果沒有四念處自我觀照的工夫,而深知自己到底是在「做甚麼」,布施了一輩子仍可能是一個極自私的人。這個道理不用我多說,相信大家應皆能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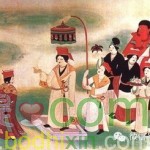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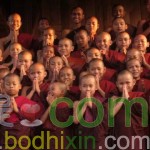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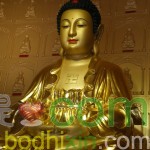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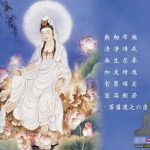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