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不離世間覺,淤泥中才能生出清淨蓮花。修行人切忌陷入玄想空談,忘卻腳下路,身邊人與事。這段文字苦口婆心,值得我們每個人用心閱讀!(編者按)
講到「性」與「相」的層次,已算是佛教中較深的部分了。但仍是在講緝起,並沒有離開佛教最基本的理則。大乘佛教所講的「性相不二」,如果用本章中所稱的形式與內涵來解釋,:就是形式雖是內涵的展現,而內涵也同時是由形式所界定。
一般講形式是內涵的展現,大部分的佛教徒皆能接受,因為這很符合較傳統的佛教思想。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當人內心中不愉快或愉快時,臉上自然就會有不悅或歡愉的表情。但當我們反過來又說內涵是形式所界定時,許多人就覺得矛盾,覺得不合理。但事實上佛教中緣起觀的看法及思想正是如此。事實上無論是「業果律」或業報思想,均是建築在內涵由形式所界定的前提上的。一切的修行及精進,也均是在確定了人的行為(形式)是會對他本身的人格及心靈(內涵)產生巨大的影嚮之後,才被悟道者提出的。
世間一切相對待的東西都是「相依」而有的,離開了其相對的東西,那樣東西本身並不能單獨存在而仍有其意義。就好像「有」要相對於「無」才能是有,「善」要相對於「惡」才是善一樣。形式要依內涵而有,而內涵也要依形式才能成其為內涵,否則容易形成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以為一切「相」上的東西都是由「性」上而生起的,而真正存在的本質是一個真常的「心」或能生萬法「性」。這樣就成了一種「單向緣起」的思想了。即相由性生,但性卻為一種本自就有的存在,如此就和佛陀本來的緣起觀法則大異其趣了。和佛說不一樣,倒並不一定是有問題。問題是一旦在最根本的理論基礎上有違緣起法則,就一定會構成一種修行上的障爵。而且也一定會在整體的佛教發展方向上,造成偏差。
唯心論思想發展到後期產生最大的流弊,就是造成修行人不註重生活與世間的一切。大家滿腦子都是一些「鏡花水月」的思想,以為眼前的這一切都只是過眼雲煙,不重要也不用太認真。真正重要的是一樣看不見但也摸不著的「性」。於是一天到晚都在修這一樣「性」,以為這樣才是有智慧。事實上這一種思想哪裡是佛陀說法的本懷?不過是末代佛法玄學化的產物罷了!
不重生活與生活中的一切而談修行,談的不是修行而是玄想。修行是一樣再實際不過的東西了,它直接的對象就是生活和生命。不重生活的修行是不會有任何效益的,因為修行所當「修」的正是生活中自己一切大大小小的行為。修四念處者不當在自己心中存有一種唯心主義的思想,以為真正重要的只是一個「內在」,而一切外在的形式皆無足輕重。如修行人有這個傾向,則當在「法念處」的觀照下,見到自己有這種思想及因這種思想而興起的行為與價值觀。見到了就要知非即離,不再為這一文化中的障礙所迷惑;當如實地在生命中觀察自己身語意行為的偏差及過失,不斷地調整自己,糾正自己,才不愧是一個修行人。否則無論你能把「二諦」說得如何圓滿,「體相用」講得如何高妙只要那個唯心主義的思想仍然存在,你整個的修行人格仍然是「迷」的;是在抓一個「性」。嚴格說來,這種行為是不能算得上修行的。
唯心論的思想加上「修行」,會得到遁世的人生態度,不但合理而且自然。我曾見到有人批評一般傳統的佛教團體皆不重組織,而不少的傳統佛教徒皆虔誠卻沒有組織能力。我以為這個看法正確但仍不夠深入,因為仍沒有看出這個現象的根由在哪裡。唯心論的思想逐漸透過文字及體系而深入到佛教文化的內層,才是造成佛教徒缺乏組織能力的真正原因。講到這裡,就又回歸到本章的主題之一——形式界定內涵了。但足具反諷性的,是此一被形式界定的內涵——唯心主義的思想,剛好講的是它本身並不被其他東西所界定。 ·
真由四念處修行下手,直觀世間與人生的佛法修行人,一定會是個有群體意識的參與者,而具有關心群體及環境的「政治人格」。中國文化發展到了後期,幾乎已有了頗濃厚的「反政治傾向」,許多人都覺得政治是黑暗的、不淨的;而把參與政治看為流俗之事。不少佛教徒更是一天到晚談心說性,哪會去關心國家的前途與社會問題?以緣起及四諦的觀點而盲,一個政治環境中的知識分子,如許多人皆有這種想法,正是該社會不和諧與無力的病態現象,長久下去是一定會出問題的。只有當這個社會的人皆能修「社會的四念處」;面能去關心這個社會的問題時,情況才有可能好轉。故當有人問我如何修四念處而能「解脫」時,我則往往會問他是否關心政治、環境維護等人類切身的問題。有人覺得我在開玩笑,其實一點也不。修四念處者,尤其是在家人,如果連自己存在環境的政治及衞生
情況都不關心,還要去講甚麼直觀人生的洞察力與臂愛的人格,豈不好笑?修行人只要對這些很近的事實漠視而滿腦子都是解脫開悟的思想,以我看就是在玄學與唯心論的人格中了。以這種心態要談佛教的四念處修行,恐怕是不大實際的!
今天我們研究佛教現代化的修行,如沒有在根本處見到許多現象與問題真正的根,則是怎麼樣也無法改變甚麼的。大家仔細想想唯心論的思想,是不是已影嚮了許多修行人的性格、行為、價值觀與思考糢式?在佛教界愈久,我愈能體認佛教真正的問題已不只是一個個人修行或理解的問題了,而是一個整個的文化層次的問題。當這個文化的內涵存在著這樣一種思想時,修行人會有這些「特質」,只屬自然。這也就又是本章所講的「內涵會影嚮形式」了。」
不只佛教是如此,整體的中國文化近數百年的發展,我以為皆是如此。道家最後講究修性修命;當然已是唯心論思想的直接代言人,而儒家經過宋明理學家的闡釋與附會後,所發展出來的思想又豈不是有濃厚的唯心色彩儒釋道如皆走了樣,成為唯心論的信徒,你能說中國沒生病,中國人不受害嗎?只是這一種「害」是殺人不見血的!思想文化上的偏差往往殺人於無形,而且大多數人皆感覺不到,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了。先儒有「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想法,其氣度是何等的恢宏,而其襟懷又是何等地入世而具人道主義的精神。我以為用這一句話點醒修行人唯心論與不重視現實的迷夢,實屬恰當。尤其是中國的菩薩道行者們,更應以這種勇於承擔的使命感自勉。否則連人間的儒者都比不上,還要談甚麼菩薩洞察三界的智慧與慈悲,就離題太遠了。
中國近代的太虛大師和印順法師,就是因為看穿了佛教發展到了後期產生的偏差和流弊,故提出了「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的理念;要修行人正視人生,用智慧與慈悲去解決人間的問題,解除眾生的苦難。我個人以為佛教徒不能有力地發揮洞察力與離執力,是二位大師的理想尚未能充分實現的原因。而唯心論的思想和人格若不能被修行人看穿並克服,人間佛教的精神是怎樣也不能在佛教徒的生命中展現的。而四念處的修行則可使人看出自己的厭世與唯心論思想,使人間佛教的理想早日實現。
故我堅決以為修行不能離開形式,而且要重視形式。修行人當活在當下而走出唯心論思想的偏差,去正視並改善人間的問題。當能在生活中修行,在人間各行各業的崗位上發揮智慧的光和慈悲的熱,去善盡自己的責任,為眾生服務。對佛陀開示的教理和修行法門要研究、實驗及尊重。有人一聽到四諦、八正道、七覺支和四念處,就站在—個頗「玄妙」的立場說這些都僅是「形式」,也就是「枝節「,而佛法真正的核心是「不離一心」的,是「不立文字」的,是「不可言說的」,是「一法通則一切法皆通」的,以為自己懂的才是真正的高等佛法。我建議有這種思想的人放下一切既有的見解.仔細去教典中體會這些佛立的「形式」的真精神,我學法至今,雖談不上甚麼成就,就從沒有發現任何理論或法門可取代四諦、八正道、七覺支及四念處的。但今日的佛教徒持以上見解的卻不在少數說唯心思想存在於佛教而造成了修行人不重形式的苟簡心理,應不僅是我個人的見解吧!
修行人只要一旦有了這一種思想,就一定落「常見」,在迷夢中而不自覺。唯心論的思想早已落伍了,只不過是一個偉大的古文化變質後陳腐的餘緒罷了!讀書人若沒有時代意識,講得好聽是書生,講得不好聽是書蟲。在20世紀資訊發達的今天研究佛法,修行人如仍不曉得原始教典的重要性,而能虛心地去體認四諦、八正道的內涵與深度,反而為傳統中種種的神祕主義及唯心論的思想聽惑,真可說是枉為現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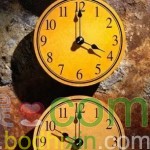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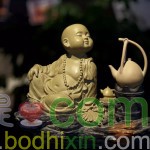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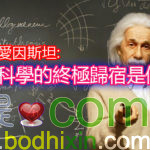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