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大家不要以為我指的神祕主義或玄學,是在指某一宗派、某一道場,或某—個人。我指的是當今佛教文化中普遭存在的一種現象。他們所形成的思想與態度,有可能出現在任何宗派、任何道場、任何個人的活動與修行中。而且所謂「文化」,它的影嚮力是具體而微的。人只要是和此文化有關,就或多或少都會有此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和心態。
所謂神祕主義,我已在前面章節中大概提過。它是一種「心態」,而不是一種思想。雖然不是一種思想,但並不意謂著有神祕主義傾向的人皆只是一群迷信者而沒有思想。相反地,許多有此傾向的人反而特別有思想。
在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中,不僅是宗教往往有神祕傾向,其他諸如文學、哲學、藝術,甚至近代的科學,其中都有傑出的宗匠有神祕主義的傾向。一個人有沒有這種傾向,給人的感覺往往是很直接的,會明顯地表現在他的生活與作品裡。近代藝術中如表現主義大師曼曲(MUNCH)的作品,就頗強烈地有神祕主義的色彩。文學中如愛倫坡;霍桑、卡夫卡,皆很明顯地在作品中流露出神祕主義的精神。故一個人是不是有此傾向,往往並不是和他的聰明才智或創造力直接相關的。許多對文學有頗深入研究的人,皆認為神祕主義甚至是文學中的一個主要推動力。而許多文學大師雖不是神祕主義的代言人,但皆在其人格及作品的一面展露出神祕傾向。像莎翁劇作中的 (仲夏夜之夢)及<暴風雨)就是典型的例子。
簡而言之,神祕主義心態意味著一個心靈對人生及宇宙中種種不可了知現象的一種回應。它並不一定是「迷惑」的;但它是一種「未定」的心之狀態。它不知不覺地架構了一個未被充分了知的心之世界,而使自己能游於其中。而未被充分了知的東西,往往就是有吸引力的,也是「神祕」的。
神祕主義的心態並不一定是完全不好的。有的宗教家或社會改革者用神祕主義作訴求,其目的是幫助他人,也做了許多善事。我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地一定要指責或批評他們。但站在佛法弘揚者的立場,我們不能鼓勵神祕主義。因為佛法講的智慧,是要修行人如實地看出人生的真相進而了解滅苦之道。以佛法的立場看;神祕主義的心態並不是「惡」,但是「障解脫道因」。因為修行人一旦精神陷入神祕主義之中,慧眼就被遮障了,人也會變得較不靈活而失去了敏銳的觀察力。此時想要他去觀察苦因及自己的種種執著,是很難的。神祕的東西像醇酒,是迷人也是醉人的。人一旦習慣性地游於其中,就像一個很輕松解除武裝了的醉漢,他的確是哲時處於一種「較不痛苦」的境界裡的。但他也是醉的,步履不穩的,不知道自己會往何處去。
人之所以會陷於神祕主義心態中,是一件很奇特並很複雜的事。至今人類學家及行為學家仍在研究階段,尚未能提出一種公認科學的解釋。站在佛法修行者的立場,我以為是有必要去用智慧看出其原因的,否則就無法離開因這些原因而生的偏執去行中道。
我以為神祕主義之所以會形成,其最基本的原因仍是因對世間最「神祕」的現象——死亡的恐懼。人因為執著於生命,但對生命現象的真實情形卻不了解,遂對「死亡」產生了種種幻想,而興起一種恐懼不安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會隨著年歲的增長而與日俱增。人間種種欲樂雖暫時能淡化這種哀愁,但同時它們也加深了人類對生命現象的執著,也就更加深了哀愁。這就是所謂「凡夫的悲劇」。
人在苦之已極的情形下,就會無條件地投入一個神祕的美好存在,使自己得到安慰。故有位哲學家認為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這種體認雖不是一件可在科學上被證明的事,但其中所蘊含的深刻智慧,是不難被有智者所了解的。
另外如人本身在生命中的「不安」及不能接受自我,也是形成其走入神祕主義的原因之一。人一旦幻想自己已進入一種超然物外的神祕存在,就能暫時地渾然忘我而得到一種「解脫」。
最後一項原因,就是人類的貪欲心。人往往有數不盡的希望,對生命有無限的要求需索。但當欲望不能滿足,或不能確定有一天會滿足時,就容易走入神祕主義,使自己得到一個無來由的「保證」——有一天自己的希望是會達到的。
又有些人總覺得現實生活太無味、無趣,總想弄出一些神奇的事才比較刺激。故一天到晚談的都是些神祕的事。這種人事實上也屑於貪欲的一型,不能滿足於現實而作幻想式的白日夢。
對於以上三種造成神祕主義心態的原因,我對第一種是抱著較同情的態度的。人在沒有由緣起去深觀五蘊而看破生死以前, 「那個苦」總是有的。有的人根性較開朗,不去想太多,故這件尚未發生的事對他的影嚮不會太大。但有人想的就較多,老是不能擺脫死亡的陰影,結果的確是頗痛苦的。這種人會投入神祕主義;減輕自己的負擔,是可以理解的。
雖然可以理解,但我絕不鼓勵佛法的修行人這樣做。因為佛法中有解除這種苦痛的方法——即所謂的「看破生死」,或「了生脫死」。佛法中所提供的理論及方法,雖不是一天兩天就能成功的,但它是一樣實際可行的東西,而不只是一個神祕的夢。在真正的佛法仍在世上的時候,修行人不去努力精進,使自己真的徹悟緣起,不著生死相而得自在,卻緊抱著一樣自己想象出來的夢境不放、以為很安全,不再怕「死亡」。這種現象實在是不可取的,是佛法衰落的現象。其他人無緣得遇佛法也就罷了,不可強求。但學佛人若不知精進,反而一天到晚迷迷糊糊地活在神祕夢中睡「生死大覺」,真是麻木已極!修行人若仍未能看破生死,則應該趕緊努力,親近善知識,務必要能將這眾生皆粘於其上的生死幻網「看破」才好。諸位能做到這樣,菩薩道才不是空談。否則這生死幻網一收一放,昨天才立了誓願,今天又不知哪裡去了。連甚麼是眾生」都不了解,還談甚麼「度」?只不過是些不切實際也不著邊際的囈語罷了!
講了這許多,大意就是我雖不反對「宗教」對人類所提供之安慰,但我認為學佛人當勤修四念處,至少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不可為神祕境界所迷,為美麗的幻境所轉。當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努力如法精進。佛法為世間眼目,要靠大家的努力才能常明。苦眾生也只有用慧眼照見生死實相,才得以真正令苦止息。學佛人就算今生不得悟,亦當於此不得悟中得不得悟之自在。見一分執著放一分,見九分執著放九分,而不作非分「非緣」之想。切不可人雲亦雲有樣學樣地跟人亂鑽亂動,陷於神祕主義之中還不自覺;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還要說自己學的是佛法,真的成了如入寶山空手回的笑柄了!
另外如有任何人因:「不安」而走入神祕主義,事實上也是頗值得同情的。眾生因缺少智慧,卻又執著於「自我」的觀念,遂產生種種不安的行為。當執著較嚴重的時候,那種不安也就成了一種苦。事實上也許因「不安」而走入神祕主義的人,比因「生死苦」而走入者反而要更多,更普遍。因為它不是一件尚未發生的事,而是—個現在的事實。
造成人的不安有許多不同的原因,但其中一項最大的原因仍是人自身的「我執」。了解緣起者知道一切皆是因緣所生,有怎麼樣的因就有怎樣的果,就不會在這流轉現象中強烈地去認定這就是「我」,或這就是「我的」。他會如實地見到哪些是缺點,哪些是執著,而心平氣和地接受、反省、改進。人若一旦強烈地在流轉現象中立一個「人我」的分際而執著其中,就往往會不能接受事實而引起不安。如老是懷疑自己很醜而不敢見人或照相,或者是覺得自己很笨而不敢在人前表達自己的想法。這些都是「不安」及「我執」強的表現。當用四念處當下照見自己身體上的緊張(身念處修行)、心裡的不安(心念處修行)及因此不安而生的那種感受(受念處修行)。照見了還不夠,還要能用四念處的離執力去放下那些執著,使自己當下就能由不安中解脫出來。若要溯本追源,修行人則
當在自己的思想觀念上作進一步的觀照(即法念處的修行),去找出是哪些觀念使自己產生了這些執著。如能用四念處的洞察力看出來了,知道是因自己很強地抓著一些「美醜」、「染淨」、「人我」的觀念而自苦,則從此就可「大安心,』了。美醜原自心生,各人心有不同。人若執著於「美」,而不能在美中亦見到「醜」,就要流浪生死受苦。修行人若不受美醜相的束縛,心得自在;則能在世間的平凡中見到神奇,無味中見到生趣。此時心中所體會到的「美」,又豈是為「相對相」所束縛的凡夫所能了解的!
消除不安,真正有效的仍是緣起正見和四念處的修行。光是靠一些心中想出來的神祕境界去自我陶醉,情況雖暫時會變好,但終非究竟解決之道。佛教徒當努力修行,使自己成為一個輕松安和的人,再以自己為例子,使其他人也能由不安轉為安和。若不能使自己輕松安和,反而學他人陷於一種精神的神祕主義中,則是佛法逐步淪亡的表現。凡我同修,能不深自警醒嗎?
至於最後一種神祕主義的因——貪欲心,則更等而下之,不是修行人該有的表現了。修行要有耐心與恆心,今天不成則明天再試,明天不成則後天該向善知請益去作自我調整。切不可一旦不成,就自己迷自己地去幻想甚麼神通,甚麼「元神出竅」諸事,終日迷於其中而不自覺。這樣就會如過去南懷瑾老師所說的成了「神經」,而不是神通了!
嘉陵居士《做個喜悅的人》連載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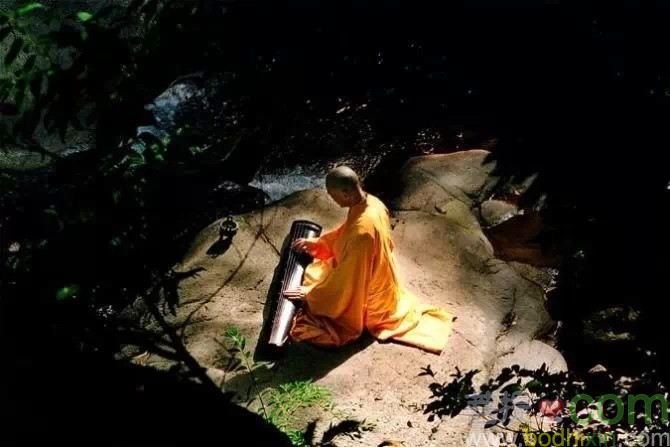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