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過這麼一個故事:一個女孩,在她情竇初開的時候愛上了一個她認為很優秀的男孩,雖然她和他並無過多的接觸。
她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看到這個男孩出現在自己的視野範圍內。他無意間投過來的一個眼神就可以讓她心跳不已,她認為他是在看自己,其實也許他只是在看她身後的那棵樹。當她不在她面前的時候她就開始想像他的一切。她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男人,既完美又偉大。她每天和想像出來的人談戀愛。
不過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那位男士的表現讓她了解到她所喜歡的這個人並非是她所認為的那樣(或者說,她所想像的那樣)。他既不完美,也不偉大,甚至有點猥瑣。她賦予他的一切美好都只來源於自己的幻想。她發現自己愛上的只是想像出來的一個人,這個人與她每天看見的那個人毫無關系。
當她發現了這一點,她對他的愛戀就徹底消失了。她不再受到幻覺困擾。這與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類似,當我們註視這個世界的時候,事實上,我們就是那個愛上自己幻覺的女孩。我們所看到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並無太大關系,可以說,你看到的只是你的心投射出來的世界。雖然世界有顯現,但是顯然它的顯現和你所認為的方式非常不同(就象你愛上的男孩和真實的男孩完全不同一樣)。
我們可以由此探討如何解脫,我們之所以有痛苦,只是因為我們執取一個不存在的自我。這實在是一個誤會。自我只是女孩幻想下的產物,與真實了無幹涉。但你卻為此瘋狂。我們不止是執取一個不存在的自我,我們還認為世界萬物都有一個我。這更加深了我們對世界的誤會。
例如,我們看見一把鎖,我們就會認為這是一把鎖。但是對那把鎖來說,他本身並無鎖的標簽。鎖的概念只是你自己貼上去的(當然你並非始作俑者)。然後你就認為這非常正確,那就是一把鎖。當其他人告訴你,那是一塊蛋糕,你就會生氣。你需要知道的是,鎖的概念和鎖本身並無任何關系,因為鎖的概念是你的心賦予的,並非它們本身就具有的。當然,這並不妨礙你使用它。
你可以審視你的周圍,當你看著你身邊的家具,你的牀,你的電腦,你的行動電話的時候,你所使用的是否是毫無染污的眼光,也就是說,沒有受到任何概念污染的眼光。如果你看到他們的時候,不假思索的就認為那是:行動電話,那麼可以說你是通過染污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事物。在顯現上,它當然具有行動電話的功能,可以通話,發簡訊,或用於偷拍別人。但是在究竟上,並無任何事物可以被認為是行動電話。因為行動電話是一個和合現象,它牽涉到無數的環節,你無法把任何一個環節省略,假如缺乏任何一個環節,它就不具備行動電話的功能,(例如,沒有信號,或沒有電池)而這些環節又牽涉到非常龐大的因果鏈,所以,如果只把它理解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在佛教裡被認為是「無明」的表現。無明讓我們只從一個習慣性的角度看事物,甚至有時候你只是從鑰匙孔裡看世界。所以你無法看到完整的世界,誤判由此產生。
了解這一點並非不重要。當一個女孩了解到她所愛上的只是自己想像出來的人的時候,她就會就此擺脫幻想,因為她不會打算和想像出來的人舉行婚禮。當你真正了解到一切事物都不是和你過去所認為的那樣的時候,你就會解脫。
當然了解到這一點並不代表你應該從此以後不再使用行動電話,佛教並不試圖證明行動電話不存在。你依然可以用他通話,但是你已經不再受幻覺困擾,一切事物的實相都和我們所認為的有所出入。不止是行動電話,電腦,也包括文字,思想,破襪子,腳指甲,牆上掛的畫,以及你冰箱裡的酸奶。如果你試著以不受任何影嚮的純淨目光來看待這個世界,你就會接近實相。不過通常這並不容易做到。
我知道有個人,當他知道他所看到的只是幻覺的時候,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當他看到蘿卜的時候,他會想:這並不是蘿卜。
這同樣糟糕。因為你同樣在執取,只是換了一個目標而已。事物雖然並非我們認為的那樣,但也同樣不是我們所不認為的那樣。認為有是錯,認為無同樣是錯,當然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也不被認為是正確的。當你遠離這四個極端,你就獲得了解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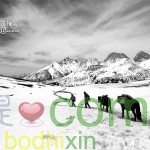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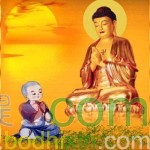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