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端午節前,南懷瑾老師在給他原配夫人的回信中,寫了一首詩:
漂泊平生負孝慈,勞君艱苦費撐持。
辜恩有愧難為報,松柏春陰應較遲。
南老師的結發妻子叫王翠鳳,實際上也是他的姨表姐,比他年長幾歲。他們的母親是親姐妹,在南老師還只有十來歲的時候,就給他們訂下了這門親事,所謂親上加親;拿現在來講,是不符合優生學的理論,也不符合婚姻法,不過當年,表兄妹結婚在溫州並不少見。他們這樁婚姻生下來的兩個兒子都很正常,很聰明,後來還生了一對雙胞胎,可惜夭折了。
南老師同他的原配夫人,雖然是青梅竹馬,但婚後一起生活的時間卻不長。南老師對她內心非常感激,稱她為「觀音菩薩」。南老師自己十七歲離開家鄉,當中只回來過兩次,在外面漂泊了幾十年,沒有機會孝敬父母親,全靠他的這位原配夫人,侍候公婆,撫養孩子。
南老師到臺灣後,初期兩岸情況一度松馳,他的原配夫人也曾帶了兩個兒子來臺相見,只是當時南老師正好經營失敗,生活困難,她們母子只得又回浙江樂清老家去了。
在以後的歲月中,特別是南老師的父親蒙難入獄以至去世後,整個家庭的重擔都落在了王翠鳳的身上,她跑到溫州給人家當傭人,一個月的工錢只有五六塊錢;兩個孩子只有十幾歲,也要出去做零工,掙錢養家。後來,王翠鳳為了更好地照顧婆婆,回老家擺小攤,維持生計。
除了謀生的艱難之外,更為嚴重的是,她的頭上有一頂可怕的帽子–「反革命家屬」,在历次運動中,都沒有逃過劫難。要不是她那種中國女性特有的堅強毅力,她自己都很難活下來;要不是她獨力撐持,她的孩子、她的家庭,不知會落到甚麼境地;要不是她的細心照料,她的婆婆根本不可能活到一百歲。
一九九0年二月十四日,是農历的除夕,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了。這一晚,溫州發生了一樁大事,南老師的百歲高堂老母,吃完了年夜飯後,忽然撤手西歸了。老太太仙逝,南老師因故沒有回鄉,他的小兒子南國熙從香港回去奔喪。
參加了喪禮的一位女士事後向大家回憶經過,最使人感動的部分,是對師母(王翠鳳)的贊美和敬佩。她說:「師母是那樣的安詳、守禮、按部就班,看到她的一切,自己真覺得慚愧萬分,我們天天說學佛,連一點師母的坦然無爭的氣度都沒有,真慚愧啊!應該先向師母學做人之道才是啊!」
老太太過世時,王翠鳳女士已是七十六歲高齡了。在這以前的很多年,她一直都是親自照應婆婆,夜裡更是同榻而眠,隨時照顧瑣事。放眼天下,不但這樣的媳婦少見,恐怕這樣的女兒也不多。這個日夜照料婆婆的媳婦,自己也早就是一個老人了啊!
對這位原配夫人的恩德,南老師自覺難以報答。老太太走了,當年的秋冬之際,南老師就辦了手續,邀師母王翠鳳女士到香港來會面。分離了幾十年,等到重新相聚的時候,兩人都已是白發老人了。重逢時刻,南老師對她說:「過去幾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過,讓你受了許多委曲折磨。」老師這樣說,可能是希望她一吐胸中鬱積幾十年的苦難,但師母卻回答說:「過去的事說它幹甚麼,只管未來吧!」這是何等的心胸和度量!一個女人,對於幾十年的苦熬,毫無怨尤,竟然一語帶過,天下有幾個女人能做得到呢!
南老師的學生們對這位師母都很敬重,熱情地帶著師母去買東西,看電影,游公園,甚至到美容院燙了頭髮。有學生還要買高跟鞋送給師母,後來老師說師母年紀大了,恐怕不習慣穿高跟鞋,扭了腳反而不好,這才作罷。對於大家的熱情,師母愉快而自然地一一接受,但總使人產生一種感覺,師母是要使大家高興,使事情圓滿。她,永遠扮演著服務別人的角色,一個慈悲喜舍的活菩薩;而周圍的我們,反而成為「本欲度師母,反被師母度」了。
過慣了恬淡鄉居生活的師母沒有留戀香港,簽證是一個月,她只住了半個月,就提前返回故鄉了。五十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兩年,再相逢只有兩周。但是她,平靜自在地回去了。她和老師在家鄉的直系子孫,已是四代同堂,她更舍不得長時間離開這些兒孫們。
還有一件讓人為之動容的事,婆婆生前,王翠鳳女士每天為她梳頭洗臉,每梳一次,都將她散落的頭髮收藏起來。後來,由發繡藝術家魏敬先先生,用這些遺發繡了一幅南老師母親的肖像。當這幅繡像交給南老師並告訴他來历時,老師激動得失聲落淚,撲通跪在母親的像前,長跪不起……
其後當太湖大學堂建設之時,也曾接師母王翠鳳女士到離太湖大學堂不遠的「淨名蘭若」小住數日,與南老師再相見,亦無所求,後來以惦念子孫為由而還鄉,實在也是不願意打擾別人。
當年,南老師於抗戰勝利後回家探望親人時,曾教師母念六字大明咒;數十年來,師母以此為念從未間斷,夢中也如是念。據說,按八字命格,師母命當出家,無子,壽數已定;而以其畢生功德與修行,感二子且延壽。
2009年4月8日(己醜年三月十三)午時末,南懷瑾先生的結發妻子王翠鳳夫人在溫州家中無疾而終,壽終正寢,享年九十四歲。
南老師親撰挽聯:
挽翠鳳妻
一身有負君情義 且付來生未了緣
懷瑾敬拜
另附南懷瑾老師詞一首,作於己醜仲春(2009年3月)
九十餘年懷舊,俱同落葉紛紛,高明庸俗盡灰塵,何處留痕。細思量,是非人我,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本是無真。但蒼茫四顧,那得容心。
(整理自《我讀南懷瑾》《南懷瑾先生側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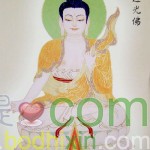










![[念佛圓通章] 楞嚴文句 勢至觀根大 蕅益大師](https://www.bodhixin.com/my/wp-content/uploads/2015/12/158-150x15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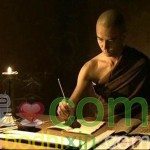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