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佛法源自修習禪坐。由此,佛陀與我們以心傳心。坐禪是去打開我們傳承的心,而我們所體驗的一切寶藏皆來自這顆心。因為要實證我們的真心或傳承之心,我們打坐修禪。
許多人一心尋找一個特別的地方,所以變得迷惑了。就如道元禪師所說:為甚麼要放棄你自己的定點,徘徊在沙塵彌漫的異域?當我們只是在觀光瀏覽,就會涉入一種想要急速求悟的心態。我們修行的方式,則是一步一步的踏實行走,欣賞我們每天的生活,然後我們能看清自己在做甚麼,處在何地。
人們通常意味習禪最好到日本去,然而那是相當艱難的。為甚麼你不留在禪中心修禪呢?我問他們。如果你去了日本,大概只會鼓勵他們興建嶄新的建築物。他們將非常高興見到你,但那花費甚多的時間和金錢,而你或許因為無法發現一個好的禪師而飽受挫折。即使你找到一個好師父,要理解他的語言並向他參學,也是很困難的。
在這裡,你能修習真正的坐禪,一步接著一步地觀照你自己。我們修行,應如一頭乳牛,而不是一匹馬。我們像一頭乳牛或大象般緩步而行,而不是奔跑飛馳。如果你能緩慢地行走,沒有任何要獲得甚麼的念頭,便已經是一名優秀的禪門弟子。
中國在宋朝末年的時候,許多禪師在回應徒弟求悟的渴望時,是以各種心理學的手法,激勵學子頓悟成佛。這些手法不是把戲,我覺得那類的修行方法有如一種策略。那些禪師可以成為心理學家的好朋友。心理學家總試著要解釋開悟的經驗,但原本修禪的法門,是完全不同於這樣的修行方式的。
道元禪師非常強調這一點,他引用中國禪宗初祖——菩提達摩與二祖慧可的故事。菩提達摩告訴慧可,你若要求吾法,入道之門是摒息外界的諸多攀援之物,並止息內在的情緒與妄念。當你變成一塊磚或是一面石牆,你便進入道了。
對慧可大師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法門,如你們所經驗過的。然而他努力修行,直到最後,他想他終於理解了菩提達摩的本懷。於是他稟告菩提達摩,在他的禪修中,功夫已經是無有間斷,永不停歇的修行著。菩提達摩說:「那麼你又是誰?是誰修行無有間斷?慧可雲,因為我相當了知自己,很難指出我是誰。於是菩提達摩印可說,你所說的是對的。你是我的法子。你明白這個故事的含義嗎?
我們坐禪不是為了求悟,而是要表現我們的真實本性。當你禪修時,即使是你的念頭,也是本性的顯現。你的念頭就像是某個人在後院或者在對街說著話,你或許在想他們在說些甚麼,但那個某人並不是一個特定的人,那個某人是我們的真實本性。我們內裡的真實本性一直在談論著佛教,不管我們做甚麼,都是佛性的顯現。
當二祖慧可大師到達此一階段,他告知菩提達摩,他想他已悟道,一面石牆是佛性,一塊磚也是佛性。一切事物都是佛性的展現。我曾經以為在開悟後,將會知道在後院說話的那個人是誰;但並沒有特別的一個人躲藏在那解釋特別教法的人之內。我們所見的一切事物,所聽的一切事物,皆是佛性的顯現。當我們說佛性,佛性是萬事萬物。佛性是我們天生的真實本性,它是普遍性的,通用於我們每一個人以及一切眾生。
由此我們明白,我們的真實本性一直在持續不斷地做一些事情,所以慧可大師說修行無有間斷,因為那是佛陀的修行,既無始,亦無終。所以,是誰在做這樣的修行呢?也許是慧可其人,然而他的修行恆常無間——它起於無始的過去,將會止於無終的未來,因此很難指出是誰在以此道修行。
當我們修習坐禪時,我們是與所有的祖師一起修行,你應該早就清楚這一點了。即使你的坐禪不是很好,你不能夠浪費時間。你或許還不知道坐禪是甚麼滋味,然而總有一天,在某個時候,某個人會印可你的修行,所以只要好好修行,不懶散閑蕩,也不做觀光旅游般的禪修,你將有加入此道,一同共修的機會。修行的好與壞都無妨。如果能用這種理解來打坐,對你的佛性具有確定的信心,遲早你會發現自己與祖師們同處一堂。
所以重點是,不以任何急功近利或求取聲名的心念來修行。我們不是為他人或為自己而打坐,我們僅只是為了坐禪而坐禪,只管打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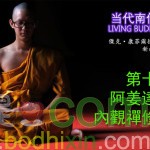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