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誤解了這個世界》序
濟群法師是我特別敬重和欣賞的當代僧人,他於我真正是亦師亦友,我受教良多,默契也良多。他人品正,悟性高,所以心態好。在佛門中,他是——用他自己的話說——一個自由主義者,超脫具體佛事,過著閑雲野鶴的生活。在人世間,他卻又是——用我的話說——一個理想主義者,然而是關註現實、惦念眾生的理想主義者,孜孜不倦地傳播人生的真理。他善於用日常的話語說透精妙的佛理,有撥雲見日之效。我本人認為,在今天的時代,他的聲音值得每一個被欲念和煩惱所困的人傾聽。
我和法師神交已久。最早是在2002年6月,他給我發電子郵件,為他主編的雜志《人世間》約稿,從此建立了聯繫。我們之間時有書信往來,但未嘗謀面,直至十年後的2012年6月,才在北京第一次見面。隨著交往變得具體,彼此更加了解,我們產生了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做一個比較系統的對話。
佛教講因緣,一個僧人和一個哲學工作者相遇在這個時代,想必也隱含著某種因緣吧。中國社會正處在轉型時期,新舊交替,萬象並呈,有一個現象值得註意。在激烈的競爭中,人們急切地向外尋求成功,但不論成功與否,卻普遍地不感到幸福,因此迷茫。其中相當一些人,已發覺問題出在心靈層面的缺失,對宗教和哲學產生了興趣,又苦於不能深入。這使得我相信,作為「專業的」僧人和哲學工作者,我們的合作對人們或許會有所助益。
人生在世,向外尋求成功無可非議,但倘若只有這一個目標,未免格局太小,境界太低。目標小而低,其結果必定是達到了沒有大歡喜,達不到則有無窮的低級煩惱。人生不可缺少大而高的目標,最大最高的目標就是向內尋求覺醒。關於這一點,哲學和宗教早有共識。中國哲學的始祖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西方哲學的始祖蘇格拉底說:「未經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過。」佛教的始祖釋迦牟尼說:「不知正確的教法而活百年,不如聽聞正確的教法而活一日。」這些教導都把覺醒視為人生的主要目標,而且在語言表述上竟也高度相似,絕不是偶然的。如果要給古今中外的哲學和宗教確定一個共同主題,便是覺醒。如果要給本書確定一個主題,也便是覺醒。讀者還會看到,以覺醒為人生的主題,這一點在佛教中體現得比其他一切宗教和哲學更為鮮明。
我和法師共進行了六次對話,時間和地點先後為:2012年6月18日我的家裡;2012年10月17日北京法源寺;2013年1月22日我的工作室;2013年12月16日北京國賓賓館;2014年7月20日北京華貿中心字裡行間書店;2015年4月21日我的工作室。近三年裡,我一直在為我們的系統對話做準備,而把這些對話視為一種預熱,不曾想到,六次對話下來,發現提綱所列的問題已談得相當充分。那麼,既然柳已成行,就不必在乎插柳是有心還是無心的了。於是,以六次對話的錄音記錄為基礎,我按照話題做了梳理,整理出初稿,法師再對初稿做認真的修改和補充,遂成本書。
和法師談話是極愉快之事。我對佛法素有興趣,但所知甚少,疑惑頗多。一半憑著無知者無畏的膽量,一半憑著追根究底的認真,我常常幾乎放肆地向法師發起「挑戰」。偏偏法師乃真性情人,喜歡有人向他「挑戰」,在傳播佛法智慧的同時,也很享受哲學愛智的樂趣。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有意立足於西方哲學的立場,像辯論賽中的乙方那樣,向甲方拋出難題。我相信,這是比一味順從更好的方式,有助於法師更活潑地啓動智慧,闡明佛理。不用說,在這種方式背後,動機仍是虛心求教,而事實上我亦大有收獲。
本書的主角是法師,我只是一個配角,全部對話是圍繞佛法這個中心進行的。我還樂於承認,即使擴大來看,在生命覺悟的領域裡,哲學給佛學當配角是一點兒也不冤枉的。和法師對話堅定了我的一個信念,即人生問題的究竟解決是在佛法之中。
文:周國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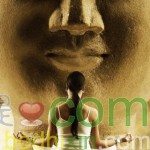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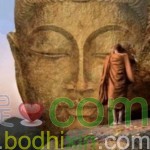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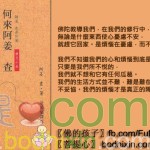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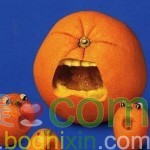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