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掬清泉,一卷白雲,一縷清風。
禪與浮華同在,當浮華遠去時,「我」在。當「我」被遺忘時,禪在。
回歸寧靜,讓我們與禪意邂逅。 ——編者
禪之意——雲在青山月在天
像竹窗外斜陽下的一黛遠山,像春日裡清新的細雨,像一個人聽壺中的茶湯竊竊私語;如風過松林,如陶淵明遇見無弦琴,如明月遇見南山下的王維。
一片茅屋,一分菜地,一卷松風,一溪水,一簾雨,一道彩虹。禪就是這樣,簡淡明淨,減去一切多餘,回歸自性寶藏。當我們隨處都能遇見來自心靈深處的喜悅時,我們就領悟了禪之意。
在眾多通往禪境的道路中,靜坐無疑是一條捷徑。生活在水泥叢林中的我們習慣了奔忙,已經將寧靜遺忘了太久。靜坐能夠讓我們休歇身心,反觀內在的生命,聆聽心靈深處的細語,發現本來就存在於生命裡的摩尼寶珠。
世間的一切原本簡單,快樂無須外求。生活其實從來就沒有煩惱和缺憾,只是我們的眼睛被蒙上了塵垢。每日忙碌之餘,在家中選擇靜處結跏趺坐,通過身與心、自我與存在的合一,體悟「不二禪境」,這就是回歸之路。
靜坐——心中的蓮花次第開放
靜,為萬物之根,一切生命都在靜態中獲得生長的力量。大地以靜謐承載山河萬靈;山林不動,以養雲嵐、飛瀑、鳥獸;樹木在靜夜裡抽出苞芽;嬰兒在睡眠裡生長。靜,是自然世界的本來狀態。
靜,也是一種心靈的境界,當我們真正安靜下來,就會與存在的萬物合一。這樣的生命不會依靠外界的「標簽」來確定自我的存在,不會因為思維和概念將自己束縛在「二元世界」裡。這種生命境界,就好像舒展在自然世界裡的幽蘭,散發出淡淡清香。生命就好像是一個不斷「破繭成蝶」的過程。每次心境從紛繁雜染回歸清澈無染時,回望前身,都會有重生的喜悅。
我們在潛意識裡都期待著自己能夠長久安住於喜樂、柔和、寧靜的生命裡。如果沒有這樣的心境,再多的名利、財富、地位也只是一個不能解脫的枷鎖。生命總會處於快樂和煩惱的輪回裡,不斷感受著得失的苦樂。我們無法阻止生命的流逝,卻可以通過修行讓心靈停止漂泊,安住當下。從喧囂回歸寧靜,需要一些必要的方法。這些,靜坐都為我們準備好了。
無茶無我,「無心」時光。
通過靜坐達到靜心,通過靜心覺知外在的世界,覺知內在的自己,覺知當下的念頭,覺知心靈的纏繞與束縛。當我們對內在和外在世界都了了分明時,才能知道如何放下妄想與執著。
我們所言的靜心,不只存在於靜坐裡,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處於這樣的生命境界,也就是禪宗所言的「生活禪」。之所以提倡通過靜坐到達靜心,是因為「心」是那樣的不可捉摸。它像一個頑皮的孩子,時而快樂,時而煩惱,顛倒反複,妄想不息。
要回歸心靈的清澈寧靜,每個人必須有一條「明確的路」。這條路不是用精神去體會和想象禪的境界,不是用頭腦去分析和理解佛經的道理,不是用語言和辯論去證明是非對錯。這條路要用整個生命去實踐,只有思想、情感、行為結合在一起,實修才能達到。在這條道路上行走,我們謂之「修行」,通過持續的修行,我們的心便能安住「禪境」。
靜心——回歸生命本來的喜悅
心不同於琴弦,本來無須去調,它與宇宙共振的頻率是相同的,皆由「自性」來彈奏。但是現在多數人的心只為外界而波動,要回到生命本來的境界裡,並不容易。人們的心不能停止攀援、占有和索取,一天二十四小時中,除了睡眠之外,多數人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註意力都放在對外在世界的覺察上。他們不了解真實的自己,缺少讓自己快樂的能力。
禪琴一味
我們說人類的眼睛生來具有兩種功能,一種用來認識外在世界,一種用來認識內在自己。多數人一生都是充分地發揮前一種,忽略了後一種。所以,只能不斷通過對外界的感知來確立自己的形象。當外界境遇順利時,就肯定自己;當外界境遇不順利時,就苦惱和消沉。
靜坐就是要把我們對外在世界的關註,收回到對內在自我的覺察上,不依賴外在世界的得失去確定「自我的定義」,讓人們的心靈培養出獨立於世間、超然於物外的態度。當外境沉陷入煩亂的人事物的糾纏時,自己的心靈能夠升起超脫的力量,不被外境所燻習和幹擾,依然保持在清澈、寧靜的境界裡。
在靜坐中培養出的心靈力量,就是掌握生命快樂的能力。無論外在的境遇怎麼改變,心靈中有一種力量是不變的。只要在自己的生命中開啓這個寶藏,就能夠對峙外在的環境變化對內心的影嚮。一個人能夠做到平衡地關註內在自我與外在世界,就能回歸生命本來的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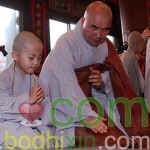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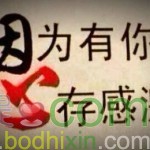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
資訊庫》 正法的傳承